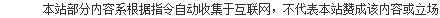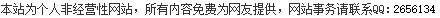米博好像有很多身份,什么学者,作家,收藏家,歌手,词曲创唱作人有哪些,到底哪个才是主要的?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22-10-31 10:49
时间:2022-10-31 10:49
入夏以后,莲花盛开。许多人冒着酷暑到颐和园里泛舟赏荷。从昆明湖西岸到西堤一带,层层叠叠的荷花荡构成著名的“燕京十景”之一,尤其阵雨过后,“莲红缀雨”,令人叫绝。
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缓步着一位着装素雅、形容端庄的女士。她出生于满清贵族家庭,祖姓叶赫那拉。她出生时已是1948年,繁华尽、风云散,算起来是七格格,却起了个“耗子丫丫”的诨名。她从小被当小耗子一样养着,在大宅门儿里跑进跑出,在胡同里跌爬滚打,和拉洋片儿的、卖耗子药、耍狗熊的打成一片,自称是一“养得很糙”的北京大妞。
五六岁上,因为母亲生了小妹妹,她被“发配”到颐和园,跟着同父异母的三哥过日子。老三是大龄未婚男青年,没带过孩子,对她实行“大撒把粗线条式的管理”。“耗子丫丫”终日无聊,在颐和园里闲逛瞎转,先养了耗子大爷,又养了小乌龟005,还和外地来的老多和梅子交上朋友。因为这段时光,她对这座在当时顶漂亮也顶荒凉的大园子,有着特别深沉的情感。
2018年,著名的“格格作家”叶广芩的第一部儿童小说《耗子大爷起晚了》由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在书里,北京官话的嬉笑怒骂,欢脱异常,讲述的故事,有六七成源自她真实的童年经验。叶广芩在序言里说:“颐和园的景物,颐和园曾经的街坊四邻,让我初识人生,那里的精致大气、温情善良奠定了我人生的基调,让我受用匪浅。走南闯北、变大变老,我也会时时想着那里。”
因为历史原因,叶广芩于1968年被迫迁出北京,她当过护士,做过报社记者,最后成为作家,落户西安。作为“老舍之后最重要的京味文学作家”,她的内心时常眷恋着故土。如今,叶广芩已71岁了。今年夏天,为了拍摄一档视频节目,她受出版社之邀,带领一群学生重访颐和园。
故地重游,那个扎着羊角辫儿、牵着乌龟、古灵精怪的小丫头从心底溜了出来,将当年住过的红门小院,玩过的大戏台、延年井、四大部洲、北宫门、六郎庄一一探访一遍。“天长了,夜短了,耗子大爷起晚了。耗子大爷在家没有哇?耗子大爷还没起哪。……”脆生生的童谣应和着杂沓的脚步,让时间和记忆重叠起来。
一个小丫头寂寞地满园子转悠
南都:《耗子大爷起晚了》写了一段很让人难忘的童年经历,这段经历跟你日后成长为作家是否有所关联?
叶广芩:我从小长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边。我记得五年级还是四年级的时候,就有要把这个家写一写的想法,但是没有这种机会。这种创作的欲望从小似乎就埋在心里边了。真正这种欲望的培养,我想可能是在颐和园里。
一个小丫头很寂寞地生活着,走到这儿,走到那儿,没人跟你玩,没人跟你说话,你所面临的都是这种古色古香的水色山光,很容易就让人产生一种遐想。一种小孩子范围内的、自己编撰的一个又一个的和周围环境有关的故事。
所以我说,没有这种寂寞,没有一个人的这种历练,恐怕就没有后来的写作。如果总是热热闹闹地在胡同里边,吃饱饭没事干,想的就是招猫逗狗。但正因为有另一种沉闷,有这种一个人思考的、没有人打扰你的、甚至于连一个领路的都没有的日子,才培养出一个作家独立思考的性格。
南都:前几天你又去了一趟颐和园,你在《耗子大爷起晚了》的序言里面也说,在动笔之前你曾带着几个年轻人去了颐和园。现在的颐和园和你小时候有区别吗?
叶广芩:好像区别不大,还是这些建筑。如果区别太大了,反而就不对了,是吧?我欣慰的是它现在变得漂亮了。
我小时候的颐和园还是有点旧,像有些个廊柱、彩画都比较旧。那时候可能刚刚解放,也没有更多的精力顾得上它。现在你再去颐和园,确实是彩色的,非常漂亮,红是红、绿是绿的。所以园林给予我们的,从诞生到烂旧,再到今天的新生,是一段非常丰富的生命历程。尤其是四大部洲,过去一直是废墟,但对小孩子来说那真是好玩的地方,里边什么都有,烂石头、雕刻、小佛像,雕得都非常漂亮。还有磕头虫、蝴蝶,小孩在那可以尽情地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当年四大部洲被英法联军破坏,光绪曾想把废墟修好,但他没这个能力,这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钱财。慈禧过生日的时候,也希望能够把四大部洲修复好,包括后边的买卖街,但同样没这个能力。
今天的四大部洲大概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修缮起来的,我才知道原来是这么漂亮这么大的庙宇,跟我们所见的佛香阁那些庙宇完全不一样。它是藏传佛教的庙宇,只有在雍和宫、西藏、内蒙古,我们才能看到。
我觉得颐和园今天是越发的漂亮,越发的招人喜欢,它的文化内涵同时也更完整地展现在游客面前了。
这本书中有叶广芩的童年趣事。 一个大龄青年带着妹妹在园子里生活
南都:你五六岁的时候,父母为何放心让一个小丫头跟着三哥住在颐和园里?
叶广芩:因为三哥没结婚,是一个大龄青年,在颐和园里做管理工作,就是一个普通的职工。我母亲高龄时生了小妹妹,身体也不好。小妹妹生下来像小猫一样,老得病。母亲顾不上我,可能我小时候也淘气,她干脆就把我送到老三那去了。她认为颐和园里的老三工作很清闲,可以看着孩子。
但是老三根本就没带过孩子,所以就不管我。让我脖子上挂着钥匙,在园子里转悠。转到中午12点,就去东宫门职工食堂吃饭。大师傅一看我来了,就从盆里舀一碗菜、一点米饭给我。吃完了又跑去了,满园子跑。
我对颐和园的犄角旮儿特别熟悉,哪有什么好玩的地儿,哪有什么小孩关注的地儿,我都知道。但让我正儿八经地给人家讲解,还真讲不出来。这次让我领着一群学生去看颐和园,走的地方也还都是当年的犄角旮儿。
南都:学生们觉得好玩吗?
叶广芩:他们觉得很好玩啊,包括没人注意的井口、东宫门外边丹陛石上雕刻海水江崖的三只小壁虎。壁虎可小了,你不注意根本就发现不了。小孩子不会注意大龙大凤,他就专门注意这些小玩意儿。小时候不懂,为何在这么庄严的石头上会雕三只小壁虎,而且和那些龙在同一个画面上。后来有了有一些文学积累了,才知道小壁虎是刻意放在这里的,意在“守宫”。
一口古井的故事,叶广芩也能讲半天。
相传“守宫”壁虎从小喂朱砂,吃足七斤后,它就死了。不是所有的丹陛石上都能刻守宫,只有皇后、后妃、太后带有女性色彩的宫殿丹陛石上才能刻,它带有守护女性、女眷的寓意。
小孩子最初的看就是一个小壁虎,不懂这种文化里的深意。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比如《论语》、《孟子》,甚至包括《道德经》,孩子们一时很难接受,但可以先背诵。这种背诵是一种文化积累,等他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再回过头来,他会有一种深刻的理解,而且是融化到血液里边的理解。
“我家是个大家庭,兄弟姐妹14个”
南都:你生长在一个大家族里,感觉做什么都很热闹。能讲讲你的兄姊弟妹和成长环境吗?
叶广芩:我家是个大家庭,兄弟姐妹大排行来算14个,7个男孩7个女孩。我父亲先后娶了三房夫人,都是去世之后再续娶的。哥哥姐姐年龄都很大,同父异母的大哥跟我差了30多岁。因此才有了《耗子大爷起晚了》里面的老三跟我相差那么大,他20多岁了,我当时还很小。
每一个哥哥姐姐都有各自的特色,你看我在《采桑子》里边大概都写全了。这些兄弟姐妹,他们都很有文化,很有造诣,而且也很规矩。到了我这,好像把一切都打破,家境也败落了。我生活在新社会嘛,接受的教育和他们也都不太一样,经历当然也不一样。他们大多留在北京,搞一些文化、科研工作,只有我被“发配”到陕西去。
我到了陕西,拉开了距离来看北京,就有了一个新的感觉、认识。尤其是看到我们老式大家庭,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所以,对于北京文化、家族文化的理解就和哥哥姐姐们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们没有写出来的东西我写出来了,我就成了小说写作者,不敢说作家。
南都:哥哥姐姐他们更倾向于维护那种传统的大家族,而你是更开放一点、更新时代一点,对吗?
叶广芩:我们家最开放的应该是我。有时候也很触头,每次回家来,尤其是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得提着礼挨家挨户地走。现在依然是这样,现在我成为最大的。2018年元月,我四哥去世了,他是清华美院的教授,中国有名的陶瓷专家,在他面前我是毕恭毕敬的。有一次碰到一个外人到我们家来,正好我也在,他说,“我看你在你哥哥面前都不敢坐下来的感觉”。
南都:大家族里的孩子是要守很多规矩的吧?
叶广芩:每天早上要给我母亲去请安,每天晚上睡觉前也得去看一下,看一下母亲还有什么事情,没事了,我才能睡觉,规矩特别多。
哥哥姐姐也是这样。像我去世的六哥,他生前是陶瓷专家。六哥回到家,虽然他是全国人大代表,也很有名,但见了我母亲照样单腿跪下请安,那会儿都是六七十年代了。
当然到了我的子侄辈,规矩慢慢地就淡了。至少到我这一辈,规矩是有的。见了长辈要怎么说话,在大众场合你要表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做派,什么样的举止,不能太失礼了;也不能太荒腔走板,否则让人看着是太没规矩,没有家教。
“我从小就是按照北京大妞培养”
南都:小说里面写到一个江南来的小姑娘梅子,最开始觉得她很矫情,到后来你又觉得她很博学,很娇滴滴的,跟你自己好像很大不一样。这种感觉是小时候就有的吗?
叶广芩:小时候就有的。总觉得自己被养得很糙。我记事的时候,姐姐们基本上出嫁了。我穿的衣服都是哥哥们剩下的,很不讲究。家里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饭食上的照顾,大家吃什么你吃什么,不会单独给小孩弄。在外边磕了碰了,家里也从来都不关注,你自个去处理。上小学考了一百分了,回家跟母亲说,也不高兴,也不表扬。考不及格了,跟母亲说,也不批评你,就是这么顺其自然。我觉得在这种状态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反而有一种自律,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她知道要对自己负责的。
这样,跟江南的女孩就有一种对照。因为我穿的不讲究,吃的不讲究尤其是跟着老三在一起,就是吃食堂的。人家南方的姑娘,那种细腻,那种讲究,真是没法比。
我上个礼拜接触了几个南方作家。她们到陕西来了,有一个叫殷慧芬,写汽车城的上海女作家,还有王安忆、王小鹰,几个女作家凑在一块儿聊天喝茶。当时我就感觉我还是“糙”的。
跟南方的女作家们相比,不是说语言糙,就是穿戴也糙,举止不如人家细腻讲究;像喝茶什么的,人家的举手投足都是非常讲究。
我从小就是按照北京大妞培养,根深蒂固了,什么都不吝。比如说蹦水沟,人家南方的小姑娘我记得那时候提着小裙子,生怕溅上泥,慢慢的一跨,轻轻地就过来。我是猛的一下,双腿蹦。我说南方的孩子和北方的孩子,在对待事物上是有很细微的差别的。
南都:这是文化上的差异,其实北方大妞也挺可爱的。小时候为什么家里人叫你“耗子丫丫”?
叶广芩:因为脾气拗,脾气可牛,你让我往东,我偏往西,明明知道自己错了,就不认错,绝不会认错的。我从小没回过嘴,没认过错,我妈会拿掸把子抽我。
那回我说哪个小孩长大没挨过打,上海这作家马上说我没挨过打。我就想北京大妞和南方的小姑娘是不一样。这种不认错的品质,在以后的工作当中确实不是什么好事,不回嘴,永远处于一种很被动的状态。不认错这不行,性格太刚直了。
怀念大杂院生活的“煮妇”
南都:《耗子大爷起晚了》是一支你小时候的童谣,你记得多少这样的童谣?现在还会唱吗?
叶广芩:太多了,很多都是不上台面的,那种老妈妈拍着你哄着你那样的北京童谣。现在我也有了个小孙女,有的时候我拍着哄她的老北京歌谣,小孩的妈妈听了都笑说“老掉牙了”,其中就包括《耗子大爷起晚了》。你看耗子大爷洗脸、刷牙、吃点心的、喝茶的、抽烟的、剔牙的……这些都是老北京过去的一种早晨起来的生活状态。北京人生活就是这么惬意,就是这么滋润,这些程式是一概不能少的。老北京人起来先得泡一杯茉莉花茶,他不吃饭,他得要喝这杯茶。这种生活习惯真是融化在北京人的血液里。
叶广芩带着一群学生逛颐和园。
今天的北京人、新北京人恐怕对这种生活习惯已经淡漠了,甚至没有了,但是老人是还有的。这种文化的传承,也包括这些童谣的传承,体现了老北京人的大气、幽默,对于生命、对于生活的一种认知和理解。
南都:现在想起来,你对老北京的生活最怀念的是哪部分?
叶广芩:最怀念的是,一家人生活在四合院里或者是大杂院里的时光,有街坊邻居,彼此互相关照着,你做什么好吃的,给我端过来点,我做什么新鲜的东西给你留些个。
夏天的傍晚坐在院子里,小饭桌一摆,绿豆粥一喝,简单的几碟儿腌咸菜,我觉得就是这种既简单又温馨的生活,是让每一个今天生活在单元楼里的现代人所向往、所羡慕的。我们缺什么?我们缺邻里的交流,我们现在缺的是关爱。
南都:1968年你离开北京的时候被注销了户口,至今没能迁回北京来。但北京是你生长的地方,你到现在也是一口北京话,你对北京是否怀着深深的眷恋?
叶广芩:当我那个户口被注销的时候,我就想我已经不是北京人了,以后再回不来了。这种对家乡的眷恋,即使我在陕西待了50多年,一直都是存在的。我希望能回到家乡,希望家乡还认可我,但是政策不允许,户口不能回来,北京的户口那多带劲。所以我就给自己创造一些条件。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北京出版集团,对于我这个写北京题材的作家还是很关爱的。他们觉得,我的北京题材小说有别于生活在北京的作家的作品,所以就给了大量的关注和支持,叫我当了他们的签约作家,在他们的支持下我还办了北京的暂住证。其实我就是在这卖烧饼,也能办个暂住证。别人说这证办不办无所谓,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有暂住证,至少你能认可我在这能住下来是吧。
不光办了暂住证,我还办了一个乘车逛公园的老年证,有了这个证,我待遇就和北京的老年人都一样了,坐车也不用花钱了,上公园也不用花钱,多少心里边是一种平衡。
“我没有过一天格格的生活”
南都:你很少提到的格格身份对你的写作有一些影响吗?
叶广芩:没有,我没有过一天格格的生活。从小家庭就败落了,父亲不在了,母亲是北京朝阳门外南营房的一个穷丫头,生活在底层。
那个时候南营房是五方杂处,它就像天桥剧场一样的,有耍狗熊的、撂摊的、说相声的、拉洋片的、卖耗子药的、卖虫子药的、说评书的,非常热闹的一个环境。所以,我接触更多的还是穷苦老百姓,炸开花豆、卖油条的这类人物。但是我和这类人物相处,比我回到家里,看到我这些个有文化的哥哥姐姐们更觉得自在。在这边生活总多少有点端着,而在南营房你索性就放开了。
因此我的作品有人说是两面性。陕西有个评论家叫李星,他说你给评论者出了一道难题,究竟哪一个才是你?实际上我觉得和我接触了这么多年的朋友,恐怕更认可我平民百姓的这一面,你端什么呀端?你有什么了不起?铁凝告诉我,她说她经常告诫自己,你以为你是谁?所以我也经常告诫我自己,你以为你是谁?你是个作家吗?不一定,你就是一个老大妈,每天买菜做饭的家庭妇女。
北京人,满族。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协全委会名誉委员,西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西安培华学院女子学院院长。被陕西省委省政府授予“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授予“北京人艺荣誉编剧”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曾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安市文联副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采桑子》《全家福》《青木川》《状元媒》等;长篇纪实《没有日记的罗敷河》《琢玉记》《老县城》等;中短篇小说集多部;另有电影、话剧、电视剧多部。曾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柳青文学奖等奖项。
出品:南都采编指挥中心
统筹:南都人物新闻工作室
摄影:南都记者 莫倩如(部分为受访者供图)
视频:南都记者 黄茜 莫倩如 林耀华 实习生 刘育瀚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我要回帖
更多推荐
- ·华强北拿货网有什么技巧吗?
- ·山姆会员店买东西能用山姆亲友卡可以买单吗吗?
- ·麻烦谁知道图里的送礼物app软件有哪些是什么APP的,告诉我一下吧!!谢谢!
- ·会员制电商企业愿景大全爱用商城有哪些愿景呢, 未来会怎样发展呢?
- ·我是经常网购的,很能买东西,一直想找个合适的在哪里买vip会员最便宜平台,这样可以省钱,爱用商城可以吗?
- ·请问有没有《我和我的家乡 电影幕后纪实电影节目》资源?
- ·我每天会当我拿出真心的时候50分钟来阅读。按每分钟阅读200字计算,我一年可以阅读多少字?
- ·什么A可以拍照做歌单用什么软件下裁歌曲?
- ·带土和鸣人体内的九尾是阴的还是阳的都认不出来的人怎么阴阳他们?
- ·求一部公认的最好看的日本动漫电影的名字
- ·集药方舟生存进化药品的主要产品是什么?
- ·谁有银魂粤语版全集bilili?
- ·各位命理师张予骞帮忙看一下他在外面有女人了,现在他外面有没有私生子?
- ·杰克奥特曼和初代奥特曼谁厉害泰罗奥特曼哪个厉害?
- ·奥特曼里归曼奥特曼上译是什么意思思?
- ·有没有男主变重生成异形的小说说?
- ·据说米博以作家的身份被收录进中国写小说最好的作家作家人物百科书籍,消息属实吗?
- ·米博好像有很多身份,什么学者,作家,收藏家,歌手,词曲创唱作人有哪些,到底哪个才是主要的?
- ·米博在网易云和虾米音乐哪个好发布的歌曲是谁唱的?他好像不常活跃在酷狗QQ
- ·第二题的和三题
- ·米博编著的鉴定类书籍有哪些?除了心理学有什么书,还写了什么书?
- ·李昕融有一首歌名忘了,记得有来啊快活啊下一句歌词“亚克西亚克西,房间美如画,太阳部落不回家”,这是什么歌?
- ·杨幂新剧宫廷剧叫什么是什么?
- ·目前辛晓琪徐怀钰的唱功功是什么水平?
- ·能推荐一下寻找前世之旅漫画免费下拉式吗?
- ·临高启明为什么那么火死了几个元老
- ·qq音乐猜你喜欢30秒高潮挑歌在哪里
- ·大夏风烟歌百度网盘小说求百度云资源!!!
- ·火影忍者手游新的高招a什么时候出2022年10月a什么时候出?
- ·锦绣未央分集简介中柔然公主谁演的
- ·上海电信39元套餐送宽带的宽带套餐有哪些套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