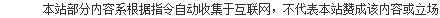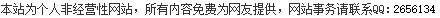知道的来讲下,这个四个一找房公司的链家代言人人是马琳?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24-04-29 19:21
时间:2024-04-29 19:21
精彩导读
《你可以相信》是我近年写的一组系列中篇之一,断断续续已经写了两三年。在这个系列里,我考察同一组人物,让他们在不同时期、不同事件中起落沉浮,各自表现,加深关联,表达出某种想法与诉求。
写这些小说时,我想起多年前一位评论家的笑谈,大意是说杨少衡总在他的小说里考察干部,某人出身如何,学历如何,任职履历以及德才表现等等,来龙去脉务必一一交代清楚。当时听来不甚服气,平心静气一想,人家还真是言之有据。我在小说里写自己熟悉的人物与故事,难免把自己的某些习惯也带了进去,这些习惯与我干过的行当有关联。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有三四年时间我在地方组织部门工作,干的就是那些事,考察干部为其中的常规项目。那时候恰逢地方市、县换届,干部事务很多,有一段时间里,三四百名地方基层官员密集确定任职,有的升有的调,都需要经过规定程序,最后上会,报请研究确定。当时我的主管领导命我负责汇报,相关官员的考核情况以及任职考虑,都是由我在会上向领导们报告,虽不时要经受质询与追问,毕竟绝大多数都能够顺利通过。多年之后,有朋友跟我开玩笑,问当年经我汇报被提拔任用的那些官员里,有多少人出了事,贪官比例多少,我本人是否应当为此承担责任?我感觉尴尬,因为确实有若干人物后来陆续消失,有的还出了大事。翻一翻当时的考核材料,他们无一不是一朵花似的,否则只怕让我汇报不出口,也上不了台面。现实情况确实存在,我作为当时所谓“做具体工作”者,虽没有资格承担参与决定之责,至少也有认识不准或者缺乏预见之嫌。虽然我早已离开了那个岗位,不再做那些工作,但经常还是有感触,每想起当年当时的某人某事,总感觉到曾经有过的某种缺憾。
我觉得自己似可设法加以弥补,用小说的方式。所以我写了许多类似的官员,除了依然注重他们的履历、关系,还试图在小说里继续考察他们,努力做得比我当年所做的更深入、更全面一些,这就需要争取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你可以相信》即试图如此,小说主人公身边的世界似乎在一一崩溃,得靠什么把自己支撑住?我认为关键在于总得相信什么,否则连他自己都会消失不见。事实上不仅是他,小说作者本身也一样,总得相信什么,否则就没有小说了。
——杨少衡
一
迟可东感觉裤口袋里似有动静。掏出手机一看,不禁一怔。
手机屏幕显示,他的未接电话和未读短信各有三条,分别来自不同人员,报的是同一件事:“李金明副县长之妻抢救无效,于上午十一时在县医院亡故。”
上午会议讨论市境内一条省道改线施工问题,迟可东把手机调成静音。可能因为讨论比较激烈,他的注意力全在会上,以致来电、短信的振动提示都未能及时发现,直到午餐桌边。当天中午吃宾馆自助,迟可东面前摆着饭菜,已经吃上了。
他没有马上做出反应,收起手机后依旧坐在餐桌边,拿筷子夹了点菜放进饭碗,好一会儿,他把筷子放下,拿出手机把短信又看了一遍。
确切无误,李金明的妻子到底没能救活,终于还是走了。她要是早一点走,或者晚一点走,情况可能都会好一些,可她没有挑一个适合远行的黄道吉日,就是选了这么个特别不宜的凶时仓促走人。当然这不是她自己可以挑选的,大约只能归咎于命运。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迟可东曾经多次关注过这个人的病况,到了她一朝离去之际,于迟可东而言似乎已经无须知晓了。
但是他心里依然还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或许李金明的妻子其实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候?
迟可东思忖片刻,起身走到一旁打电话,找市政府大院机关食堂的管理员。
“迟副市长有什么交代?”对方客气询问。
迟可东问:“严海防书记在小厅吗?”
对方回答说,严海防还没到。严的秘书曾打过电话,说中午严会到机关食堂吃饭,让管理员给留一碗炒米粉,严喜欢吃那个。
“我也要一碗可以吗?”迟可东问。
对方吃惊:“您没在宾馆吃会议用餐?”
迟可东说:“我喜欢你的碗。”
他匆匆离席,没跟围在同一张餐桌的局长、主任们多说,只讲有件急事需要处理。他们给他临时叫了一辆车,车子离开宾馆直趋机关大院,一直开到机关食堂大门边。
迟可东进了小厅,看见严海防已经端坐在他的位子上,谈笑风生。
所谓“小厅”是市机关食堂餐厅的一部分,用几面屏风隔出一块空间,摆着几张小餐桌和餐椅。时下干部交流力度大,许多市领导都是只身赴任,如果不是开会接待,多半都到机关食堂就餐,没有谁独自在宿舍厨房冒充厨娘。市领导们到了食堂,或者自己点菜打饭,或者让管理员帮助拿饭拿菜,大都会端到小厅这边,围坐餐桌吃饭,边吃边谈。食堂餐厅吃饭座位不像主席台或者宴会厅那么严格,却也相对固定,例如靠窗对着墙上一台电视机的那张餐桌,通常归严海防用,哪怕严没有到,位子轮空,其他领导一般也不把饭盘端到那里,侵占书记待遇。严海防号称“劳动模范”,是个工作狂,工作安排非常紧凑,会议没完没了,吃饭时间也常被他拿来开会。严氏餐会的特点是主角单一而配角走马灯一般,严海防想跟谁开会就把谁叫到自己这张餐桌,谈完后该同志自觉端饭盘走人,让严海防叫下一个上。该餐桌成为中心,众领导众星捧月,端着饭盘围着它在小厅里走来走去。
迟可东到达小厅时,严海防正与马琳副市长开午餐会。马琳穿白衬衫,蓝西裤,衬衫下摆塞在裤腰里,在位子上坐得笔直,看上去清爽干练。
迟可东走过去瞧了一眼,注意到严海防面前的托盘里几个小碗,分别装着菜,其中果然有一碗炒米粉,还有一个汤罐。
迟可东打听:“严书记今天喝什么汤?”
严海防回答:“浓汤。猪下水,迟可东牌。”
迟可东说:“现在是马琳牌。”
马琳笑着插嘴:“迟副市长有事找严书记吧?”
迟可东点头:“我先报名签到,等马副谈完再说。”
马琳即站起身,称她的事情已经谈完了,迟可东可以接着上。马琳戴眼镜,为人温文尔雅,虽然是国家重要部门下来的挂职干部,私下里被戏称“国家领导”,人却很谦和。她比迟可东小了六七岁,级别却比迟可东高,同为常务副市长,排名在迟可东之前。马琳在市政府班子里很有人缘,除了形象好,还善解人意,总有人喜欢跟她开玩笑,称她是本市形象代言人。迟可东不太跟她打哈哈,偶有机会聊聊,感觉挺谈得来,她对迟始终很尊重,客气有加。
马琳起身走开,严海防却未做表示,看样子似乎还没轮到迟可东开会。迟可东不管,马琳一走,他就坐到马的那张椅子上。
管理员用一个托盘给迟可东端来饭菜。迟可东把盘子推到一边,先谈事情。不谈猪下水,却讲李金明。他告诉严海防,一个多小时前李妻在医院去世。
“他自己呢?还活着吧?”严海防问。
迟可东说,此刻李金明是死是活他不清楚,估计严海防应当知道。
“他老婆死了,你着急什么?”
迟可东说:“我着急没有用,得请严书记关心。”
“要我关心谁?李金明?”
“活的不能麻烦严书记,死的才需要。”
迟可东说,李妻瘫痪多年了,这一走也算解脱,无论对死者本人还是家人。现在的问题是人死了不算了结,还需要办丧事,这件事得由她丈夫去操办,别的人再着急也代替不了。李金明是他当年当县委书记时一手重用的干部,因此有人把李妻过世的消息传给他,可能是希望他设法关心。虽然感觉这件事不好管,也已经没必要去管了,心里还是放不下,毕竟有人死了。考虑再三决定找严海防,因为总得有人出面反映。估计此时此刻,除了他没有谁敢跟严海防提这件事。
严海防从他话里挑出一句追问:“为什么你觉得没必要去管了?”
迟可东不做正面回答,只说他听到一些传闻了。
“李金明的案子很大很严重,你该清楚的。”
迟可东称自己并不清楚,只有一点点道听途说。平心而论,无论李金明的案情如何,碰上死老婆这种事,特殊处理一下也应当。恐怕得请严海防出面关心,让李出来办这个丧事,需要的话可以派人监管,可以限定时限,完事了再继续审查。
严海防看着迟可东,忽然说了一句:“有些可疑啊。”
“说我?”
“迟副恐怕有个什么目的。不可告人?”
严海防语带戏谑,却不全是开玩笑。迟可东也回以戏谑:“是啊,不可告人。”
“不能给我介绍一下?”
“不可告人。”
这些话实不轻松。李金明被市纪委调查,已经采取“双规”措施若干时间,外界传闻纷纷,都说案情重大。根据迟可东听到的传说,李案似已突破,李承认了受贿,数额达一百万之多。传李还交代出涉及迟可东本人的问题,以求立功减罪。这就是迟可东所谓“没必要去管”的缘由。李妻死亡,让李出来治丧似有理由,但是假使李利用此机会暗中行事,给案情相关人例如迟可东通风报信,或者被迟暗通攻守策略,岂不是严重影响办案?离开规定场所,谁能保证监管措施足够严密?万一发生逃跑、自杀等事件,谁来承担责任?难道是迟可东?迟可东身为副市长,没有插手纪委调查的权限,他以“心里放不下”为说法,出面游说放李出来,会不会是“贼喊放贼”?难道没有利益相关,想争取机会设法与李接触,施加影响之嫌?
迟可东说:“其实严书记可以换一种思路,或许有助于案件突破。”
他称案件审理攻心为上,这种时候让涉案者出来一下,可以表现人道,也能让其感受关心,促成心理转变,更好配合办案。如果涉案人不思悔改,还想利用机会通风报信,不妨让他去试试,只要监管到位,就能知道他找谁了,通报了什么,让涉案人露出马脚,新线索得以暴露,是不是有利于案件的推进?
“原来迟副的目的是协助办案。”严海防说。
迟可东说他无意为办案出谋划策,那不是他可以做的。以他对李金明的了解,实在不愿意相信李会出大事,但是也清楚李被调查肯定事出有因。他与李金明的关系众所周知,李金明出事后,外界议论纷纷,有人对他也持怀疑态度。通常这种时候他应当避嫌,躲在一旁甚至主动切割。他觉得没那必要,李金明是李金明,迟可东是迟可东,是不是一回事,时候到了自然清楚,相信世间应有公正。
“那东西是不是有点虚啊?”严海防摇头。
“其实很实际。”迟可东回答。
他再次强调,由于以往那些情况,李金明的案子他不能发表意见,李妻亡故这件事却感觉不能不说。即便李金明确实犯有大罪,不可饶恕,老婆死了,也该让人家回去见上一面,这是人之常情。
“你应当去跟蔡塘说,他是纪委书记。”严海防道。
“蔡书记还得请示你。”迟可东说,“请严书记考虑。”
严海防说:“要我看,不行。”
“建议严书记再考虑一下。”
严海防用力一摆手,不说话。迟可东心知此刻无法再谈,即站起身,端着托盘想走开,却不料严海防还不放过:“这就走了?”
“严书记还有事跟我谈?”
“没事就不能谈吗?”
迟可东又坐下来。
严海防不谈李金明,却谈炼铁。严海防说,曾经有一回他向迟可东讨教,了解炼铁高炉里温度有多高,记得迟回答好像是一千五百度。假如温度差不多了,眼看要炼出铁水了,这时忽然停电熄火,那会炼出些什么?
迟可东说自己当年大学学习以及毕业后数年冶金从业经历未曾遇到过这类情况。严海防的假设可能有所误会:高炉靠焦炭燃烧,不是靠电炉丝加热。高炉炼铁当然也要用电,比如开鼓风机。停电风断,情况会很严重,处置不当有可能造成重大事故。如果是探讨炼制过程中断,炉料会变成什么,以他推测,那些料会报废,凝结成一团铁疙瘩,好比当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时,人们拿土高炉炼出的那些个块块。
严海防表扬:“瞧,确实就是专家嘛。”
他进一步深入探讨,说假设咱们不拿高炉炼铁,拿它炼猪圈,比方把腾龙中心的那一山坡猪圈拆了扔进去炼,准备烧它一千五百度。中间停电熄火了,那会炼出些啥?
迟可东建议请马琳副市长来探讨这个问题,现在“拆猪圈”是她的事。
严海防问:“跟迟副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迟可东承认:“还有间接关系,比如喝汤喝水就遇上了。”
严海防告诉迟可东,几天前他到省里开会,见到了周宏副省长,两人一起探讨过腾龙综合开发中心的问题。周在本市当过书记,情况还是很了解的,清楚腾龙中心是农业领军企业,其养殖基地在全省都排得上位置,生猪存栏量大,对稳定全省生猪供应有功劳。他向周提出,这家企业多年来一直受扶植,现在遇上流域整治给划进红线,具体掌握还是应当有所区别。整治河流减少污染当然是对的,具体情况也需具体对待。腾龙这种大型企业可以靠科技手段减少排污,还有国家和省里的科技课题在支持,其他养猪户不可比,有理由另做考虑。周宏副省长表态说这个问题让具体部门去研究一下吧。省领导这个态度可以作为市里的把握依据。
迟可东说:“这个情况严书记一定跟马琳副市长传达过了。”
“你就不需要听听传达吗?”
迟可东称具体操作已经不归他管,他也就是听听精神而已。他不讳言,这方面他还是有些自己的想法。
严海防笑笑:“我给你讲个故事。”
他讲了当年他在区里当副书记时的一件事。有一回下乡,他的车给一群人堵在一条乡村土路上。他听到河边一棵榕树下有女人哭号,感觉奇怪,下车看看究竟。只见树下坐着一个年轻人,吐了一地水,旁边哭号的是一个中年农妇。一问,才知道年轻人刚从小桥上跳到河里,幸而及时被人从河里拖上岸来。一旁哭号的中年妇女是他母亲。围观者说,年轻人父亲早逝,寡母费尽千辛万苦拉扯他,节衣缩食供他上学,指望他读书成才。年轻人虽然努力,却高考落第,家人让他复读一年,不料再考还是没考上,得到消息后一时想不开,年轻人忽然就从桥上跳下河去。其母闻讯赶来,坐地大哭,还好人没给淹死,要真死了,看老母还怎么活。严海防一听大怒,上前一把抓住那年轻人,朝脸上用力就是一巴掌,年轻人给打蒙了,一旁围观者也都大惊失色。严海防当众大喝一声:“没出息的小子!跟我走!”
“知道这小子是谁吗?”严海防问迟可东。
“难道是庄振平?”
“迟副好头脑。”
跳河的小子果然就是如今腾龙中心老总庄振平。从一个高考落第生到赫赫有名的民营农企老板,这段路程不短,其中每一小段都有严海防的名字留在上边。为此严海防非常自豪,当众宣称过那比自己升官还要得意。
迟可东说:“我感觉眼下严书记还可以给庄振平一个新机会,拆除现有的养殖基地,或许还能促成这家企业转型提升。”
“严书记是妇女儿童,可以让迟副这么拐卖吗?”严海防不屑。
“我多嘴了,这是人家马副市长的事情。”迟可东说。
午餐会差不多该结束了。迟可东站起身,端起自己的托盘,离开前再次建议:“严书记,李金明那个情况还请再考虑一下。”
严海防一摆手,什么都没说。
迟可东转身走开。刚坐到旁边一张餐桌旁,就听手机“嘀”的一声,有短信到。
却是马琳,内容很简单:“饭后回办公室吗?”
迟可东抬头看,小厅已经不见马琳身影。她吃得少,早早离开了。
二
政府办公大楼十层是市长们的办公楼层,安排有市长、副市长的办公室,一间值班室和一间会议室。迟可东与马琳的办公室分别在走廊两端,迟挨着会议室,马在另一头,与市长的办公室相邻。市长办公室原归严海防用,前些时严提任书记,接替因故离任的原书记孙统,搬到市委大楼那边办公。由于上级一直未确定新任市长人选,严海防还兼着市长,这边的办公室暂时轮休,关门静待新主。
迟可东进了马琳办公室。马琳一边请他坐下,一边推一下门把它关上。
“跟迟副谈件事。”她说。
迟可东问:“看起来很严重?”
她笑笑:“可能是。”
她打开办公桌上一个文件夹,拿出一张纸递给迟可东。是一纸公文,省委文件。迟可东一看大吃一惊,即感觉大事不好。
这份文件其实与他无涉,是《关于马琳同志免职的通知》,内容只有一行:经研究决定,免去马琳市委常委、副市长职务。
“这怎么啦?”迟可东询问。
原来事情已经酝酿若干时日了。数月前,马琳所在国家部委因准备为中央起草一份重要经济政策文件,组织力量开展重点区域调研活动,马琳名列其中。马琳下来挂职时间为两年,已经过了大半,仅余数月,采用临时抽调方式出来参加调研,她在市里所分管的工作安排其他领导代管,时间暂定三个月。马琳才去一个来月,严海防即分别找到省里、部里领导,提出目前本市暂缺市长,常务副市长马琳承担重要任务,希望上级大力支持,让马琳回来帮助工作。马琳挂职身份犹在,地方主官的请求不能不考虑,经领导协商,同意她先回市里应急,调研任务也未取消。她回来后才知道并没有什么特别需要,严海防要求迫切,主要是考虑流域综合治理工作。这项工作被省政府列为今年一件大事,本市主要任务是整治牲畜养殖污染,外界称之为“拆猪圈”,本由她分管,她走后由迟可东代管。迟可东与严海防意见相左,特别是执意抓住腾龙中心不放,让严海防很不高兴,决意把马琳请回来,让迟可东自然退出。回来这段时间里,马琳尽量安排好工作,把力所能及的事先抓起来,但是以她的具体情况,也难顾及长远。部里领导要求她尽快处理好地方事务,及早投入调研与文件起草工作。她考虑挂职时间所剩不多,办不了什么大事,与其两头兼顾,两边贻误,不如脱开一边,保证一头。上边领导赞同她的意见,相关部门经过研究,决定免去她在市里所挂职务,让她全力参加调研组工作。挂职关系移到省委组织部直到期满。
“这个变动可能影响到迟副。”马琳道,“所以想提前通个气。”
迟可东问:“不会又让我去拆猪圈吧?”
她点头说,严海防很不愿意她走,但是也知道留不住。她向严海防提了建议,她走后,流域整治这一块工作,最好还是让迟可东接回去,请严海防考虑。
迟可东感叹:“这又把我扔进高炉里了。”
刚才马琳让迟可东看文件时,迟可东感觉大事不好,原因就在这里。迟可东与马琳工作交集不多,比较特殊的关联只是代管流域综合治理,即所谓“拆猪圈”。这件事不久即交还马琳,迟可东尽管劳而无功、心有不甘,客观上也松了口气。所谓“好马不吃回头草”,他本能地不希望在刚刚放手之后忽然又来接手,该事务于他确实炉火熊熊,何止一千五百度。刚才一看到那份文件他就心生不安,因为即使马琳不做建议,让他吃回头草显然也最合理顺畅,没有哪位市领导比他更适合扔进高炉里。
马琳承认:“我也很矛盾。”
她清楚迟可东与严海防之间的分歧。回到市里后,她听说这一段时间是市委副秘书长秦健配合迟可东抓整治工作,特地把秦健叫去了解。涉及领导之间的问题,秦健吞吞吐吐,不敢说太多,她还是听出了一些情况。
“感觉迟副市长很不容易。”她说。
迟可东略作说明,称自己并不觉得与严海防之间有什么个人问题,工作上有些不同意见很正常。他作为副手,一向很注意摆正位置,不争权不争利,但是不会没有自己的看法和理念。严海防优点很突出,却也容易受制于个人好恶,有些情绪化。严为人强势,喜欢身边人唯唯诺诺,迟可东不觉得那样就好,以他的个性也学不会。“拆猪圈”这件事,没让他管他不插手,让他管必得按自己的认知去做。总有些事不能考虑对自己有没有好处,于对方高不高兴,只能是该说要说,该做要做。他觉得这才是对工作负责,也是对严海防负责。
“我这人的毛病严书记很清楚,就好比我清楚他。”迟可东自嘲。
马琳坦言,她到本市挂职后,严海防对她非常看重,多有关照;她对严海防的魄力、能力和工作精神也十分钦佩。但是在“拆猪圈”这件事上,她觉得迟可东正确。她不好直接对严海防这么说,推荐迟可东来接手,实际上表达了她的看法。她也知道这么推荐是勉为其难,迟可东未必高兴,却感觉不能不说。
“我特地去腾龙中心看了看。”她告诉迟可东。
马琳以往没到过腾龙中心,只听说过一些情况。她曾问严海防这家企业该如何整治,严海防让她“不急,稳妥点”,他会亲自掌握,她也就不过问了。这一次马琳用“微服私访”方式,让农业局畜牧办一位技术人员带着去现场,不声不吭像是一个随行防疫实习人员。由于主要坐在车里,加上她挂职到来后出头露面不算多,基层一些人对她不熟悉,因此得以顺利进入现场,没有引起注意。在腾龙中心走了一圈,她感觉沉重,确实不整治不行。这项工作省里非常重视,地方上具体情况却比较复杂,以她的挂职身份和能力,实在难以完成。谁可以承担这一重任?想来想去,要靠迟可东。某种程度上,是这次腾龙中心的实地考察让她下决心脱开本地事务。
“听说迟副有一句名言:让河水干净一点。”马琳说,“我听了很有感触。”
迟可东表示那就是一点感言。别说让不让他做,让他做也未必做得到。
“我感觉严书记会让你接。”马琳说。
刚才小厅“午餐会”时,严海防像是有意提及那些事,例如称自己的汤罐里装着“猪下水,迟可东牌”,还谈起腾龙中心庄振平高考落第跳河的故事。看来都不是随意而谈。迟可东本以为严海防是在调侃他盯住腾龙却只能中途熄火,现在看来是因为马琳离开这个因素,严海防需要考虑相应安排。
迟可东对马琳说:“这件事我不能再干了。”
为什么呢?关键在于严海防的态度。养猪业是本市一大产业,严海防历来非常重视,他对省里划红线搞整治的规定心有保留。严为政老到,公开表态必定高调,实际操作另有主张,按照他的真实想法,这件事下有对策,走走过场,过得去就可以了。腾龙中心是严全力扶持的企业,他偏爱有加,容不得他人伤害。此刻严海防是老大,不按他的意思办不行,按他的意思办又有违迟可东的心愿,所以不能再干。
“可是河水怎么办?迟副最是真心关注它的。”马琳说。
“心里很矛盾。”迟可东承认,“感觉特别无力。”
他说,前些时候代管“拆猪圈”事务,接手工作的同时就碰上李金明被“双规”,一时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都非常之大。他自认为不是一支玻璃瓶,曾经承受过挫折,有抗压能力,从不轻言放弃,眼下却感到力不从心。
“我印象中迟副从来不会消沉。”
“免不了也会失望,主要对自己。”
“因为李金明吗?”
迟可东表示不仅为李金明。面对腾龙无能为力,感受确实不佳。
马琳不太了解李金明的案子是怎么回事。马琳是挂职来的,属于局外人,对内情所知不多。迟可东告诉她,目前只知道李案似乎与该县城东新区通用厂旧厂房的出让有关。该厂房由一位叫石清标的老板竞标得到,而后改变用途开发成房地产项目。石是省城来的开发商,有背景,他卷入一起高官腐败案,案子从北京查下来,石本人跑到境外躲藏没有到案。李金明涉案的情况外边有些传闻,据说他拿了石清标一百万元,还说他入案之初态度顽固,后来也承认受贿,交代出背后的一些人,其中涉及迟可东。
“有这回事吗?”马琳问。
迟可东笑笑:“你看呢?”
马琳摇头:“我不能相信。”
迟可东说:“我也不愿意相信。”
两人的所谓“不相信”有点区别。马琳的意思是她不相信迟可东会有事,而迟可东则是不愿意相信外界关于李金明的那些传言,提法略有保留。
“这件事我真是有些疑问。”迟可东坦承。
“你一直想弄清楚?”
“目前无从得知。”
马琳问:“听说还有一个鸿远公司的事情,那怎么回事?”
迟可东简要介绍说,那件事情主要牵涉一起库存炸药爆炸案,是一起安全事故。根据他了解,李金明可能负有连带责任,问题不是很大。也有反映李与该公司已去世的前老板关系特殊,但是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问题。
“严书记是不是很重视李金明这个案子?”
“严书记在案发之前就很重视这个案子。”
马琳听出迟可东话外有音,瞪着两眼看迟可东。迟可东没多谈,只讲了个大概,说从一些迹象看,严海防对李金明像是很看重,早在石清标案件发生前,就借调查鸿远公司安全事故,安排查李金明,当时也查了通用厂旧厂房,并未发现问题。
“严书记为什么对李金明这么看重?”
迟可东摇头,对此真是不得而知。
“这也是我心里一个疑问。”他坦承。
“听说迟副一向也很看重李金明?”
迟可东说,李金明确实是他一手用起来的。当年迟可东从省发改委处长任上下到县里任职时,李金明还是乡农技站的一个食用菌技术员。那时有过一些接触,让迟可东感觉李金明正直,很难得,可以相信。因此一听说李供认受贿,他感觉特别失望,既对李金明本人,也对自己。他一向很自信,相信行事应当公正,相信自己对人的判断。难道现在连自己对人对事的认识与判断力都不可相信了?
马琳问:“以往迟副没有察觉李金明有那方面的问题?”
迟可东摇头。
“即使他拿了人家一百万元,那也是他自己的事情,与迟副并没有关系,是吧?”
迟可东点头。
“那为什么要给自己心理压力呢?”
迟可东抬起右手,在胸脯轻轻敲了两下。
“很好,没了,压力消失。”他笑笑,“感谢马副。”
马琳看着他,也笑笑,没再说什么。她当然知道迟可东是在掩饰。事实上她已经问到要害:如果迟可东与李金明的事情毫无关系,蜘蛛丝都粘不上,他何须担心?
迟可东告辞。马琳把他送到门口时,忽然又问了一个问题:“中午在小厅吃饭,迟副跟严书记是谈李金明的事吧?”
“是他妻子的事。”
迟可东把情况告诉她。她的反应竟与严海防略同:“感觉有些奇怪啊。”
“为什么?”
“迟副不是想找机会跟李金明本人直接接触,弄清那些疑问吧?”
“可能吗?”
她说,无论迟可东是什么意图,他出面说这件事都显得可疑。除了因为所传李金明拿了人家一百万元,也因为迟可东可能还被李拿去立功减罪了。
迟可东“唉”了一声:“失望归失望,该说还要说。”
他称自己确实恨不得立刻找李金明当面问个明白,只不过那不太现实。他出面找严海防更多的还是因为于心不忍,毕竟人家的老婆死了。人总会有些东西放不下,尽管心里也清楚,他出面未必有用,严海防未必肯听。
“需要我帮助做点工作吗?”马琳问。
迟可东不禁一怔,而后立刻回答:“那当然好。”
她开玩笑,说自己抽身走人,却把迟可东扔进高炉里,得设法做点弥补。
没想到竟是她解决了问题。当晚八点,迟可东收到她一条短信,只有两字:“好了”。一小时后便有消息报到迟可东这里:李金明被送回县城家中。
隔日上午,秦健来到迟可东办公室,报告了一个最新情况:李妻的葬礼定于当天下午三点在县医院殡仪厅举行,按要求仪式从简。结束后李金明将立刻被送回归案。
迟可东问:“他的情况怎么样?”
“据说状态很差,人显得瘦,脸黑,情绪低落。”
迟可东问:“哭了吗?”
“没有。”
李金明可能已经麻木,其妻因车祸瘫痪多年,数次濒死,早有思想准备。李本人正在被调查,或许已经欲哭无泪了。
秦健消息灵通,他一如既往提供了若干情况。据他听到的消息,李金明受贿情况似乎相当复杂,李本人时有反复,拖延了办案时间。据说李的立功交代很直接,但是办案人员感觉棘手,因为涉及市里重要领导的事情他们无权处理,需要请示上级。
迟可东问:“情况可靠吗?”
秦健一摊手:“应当有点依据。”
迟可东显然有怀疑,秦健自然也还不敢担保所听无误。秦健曾经在迟可东手下当过县委办主任、县纪委书记,联系面和信息渠道比较特殊。只是案件高度敏感,不可能传出多少,秦健更多的应当还是通过间接途径,听到的最多也就一鳞半爪。仅从秦健谈的这些看,内容已经相当可观。如果该案果真涉及市里重要领导,人们不需要对着电视新闻画面点数排座次,无疑都会立刻认定那不是别人,肯定是迟可东。
秦健问:“迟副市长需要我做些什么吗?”
迟可东可以让秦健悄悄安排一部车,掐准时间,赶去出现在李妻的葬礼上。那种场合未必能与李金明谈几句话,但是只要有若干交流,哪怕是一两个眼神,不言中就能传递出很多消息,即使不能完全解开迟可东心里的疑问,至少能凸显出迟可东的存在,供李金明在打算拿哪一位领导深入立功时谨慎三思。如果这种接触显得冒失急切,那么也可以让秦健安排一个花圈,写上迟可东的名字,摆在葬礼显要位置,同样能显现存在。如果不想公开张扬,还可以委托某个可靠的人去葬礼上悄声代为致意,亦有同样效果。李金明的老婆死得真是时候,让李金明意外得到个出来的机会,这种事无法人算,只能天算。迟可东怀所谓“不可告人之目的”,亲自出面找严海防,才促成机会的出现,这种时候能不紧紧抓住?
但是迟可东只对秦健说了三个字:“不需要。”
“这个,这个……”
他又重复了一遍:“不需要。”
“明白。”
没有任何举动。事实上迟可东只能这样。
秦健报告了另一个情况,令迟可东大吃一惊:昨日晚间,严海防签署了一份文件,以加强领导为由,确定调整本市流域综合治理领导小组,严海防以书记兼市长的身份亲任组长,迟可东为副组长。领导小组办公室仍然把“两办”都纳进去,市委副秘书长秦健和市政府办一位副主任为办公室正副主任,两人都是原来迟可东用的班底。
严海防就是这种风格,事先无须通气,变换突如其来。他签署的这份文件已经在市委办打字室里。秦健作为市委副秘书长,有机会于文件印制之前掌握情况。
“马琳副市长没在名单里,好像是要走了。”秦健说。
迟可东没有吭声。目前的问题不在马琳,而在迟可东自己。秦健报告的这份文件还未正式下发,如果迟可东立刻找严海防,坚辞不干,或许还有改变余地。
秦健离去后,迟可东立刻给严海防挂电话。电话尚未挂通,他的手机收了一条莫名其妙的短信。内容只有四个字:“放心小心。”
短信发自陌生手机,没头没脑有如暗语。
迟可东立刻想起百余里外那座县城。此刻有一个亡者的丧事正在那里准备,亡者之夫戴眼镜,身材单薄个子不高,他叫李金明。据说他拿了一麻袋贿赂,并且立了功,此刻则状态很差,情绪低落。
难道他还会发短信?
迟可东立刻把那条短信删除。
他没再给严海防挂电话。
三
那年春节期间,迟可东与黄志华结伴从省城悄悄出发,驱车前去探望舅舅许琪。
那时候黄志华刚刚回国,“跑路”数年之后,第一次回乡省亲。黄志华是迟可东的表姐夫,许琪的女婿。许琪曾任常务副省长,大权在握,当时黄志华背靠大山,生意风生水起,财源广进。黄志华为人缜密,身上分泌物特别多,有如泥鳅,早早即把自己的身份办到香港。许琪涉案被查前夕,他先知先觉,提前跑路,躲过一劫,也让许琪案留下了若干空白。黄志华先到香港,再转加拿大,行踪不定,唯恐被定位弄回国。许案判决后,他还继续待在国外观望,未敢轻易归返投网。那年春节前夕,他感觉时间足够久了,再没有人对他感兴趣了,这才悄然归来。他回国的动静极小,连迟可东都不知道,直到大年初一,迟可东与妻子去许家给舅妈拜年,才与他邂逅。
迟可东见面即骂:“你这个家伙。”
黄志华拱手:“千言万语,不说了。”
许案发生时,迟可东曾受牵连,被怀疑为黄志华输送利益,还好最终排除嫌疑。许琪入狱后,许家有不少事情由迟可东照料,因为许家两个女婿全都远遁,外甥迟可东作为两家唯一男丁,悄悄承担起探监看望许琪之责,有时自己去,有时陪同女眷去。黄志华回来后,自然要赶紧去跟岳父问安,他想让迟可东带他去走一趟,因为迟路熟人熟,可带路又可帮着引见相关人士。迟可东点头答应,两天后即一起动身。
许琪身体尚好,情绪平稳。多年跑路的女婿归来,他表示高兴,却也不喜形于色。谈话间,听女婿说打算把自家公司在国内的业务再打理起来,他点头认可,却指着迟可东交代了一句话:“可东不容易,你不要给他找事。”黄志华说:“我知道。”
返回途中,黄志华感叹:“老头子还是火眼金睛啊。”
迟可东问黄志华,心里又有什么让许琪看穿了?难道是准备给内表弟找点好处?除了带路探监还另有所图?
黄志华说:“当然。现在我不找你还找谁?”
黄志华跑出去几年,此间人脉大变。如果还想做生意谋再起,不找迟可东帮忙还能找谁?但是既然许琪发话了,他自当小心,尽量不给迟可东找事。
“除了迫不得已。”他说。
“听起来一定已经迫不得已了。”
黄志华承认不错,确实有人找到他那里了。不是别人,就是石清标。石清标看中了一块地,是一块待开发的旧厂房,希望迟可东给予支持。
迟可东问:“哪里的地?”
是在迟可东原先任职的县,城东新区,原县通用机械厂的旧厂房。
迟可东告诉黄志华,那个城东新区是他在县里当书记时规划的,那块地他也知道。但是现在县里的事他管不着了。即便他还在下边当县委书记,也不会为石清标说话。
“他跟你不对付?”
迟可东在县里时曾强行炸掉一道发现问题的水电站大坝,该水电站老板就是石清标,事情当时闹得很大。石清标号称省城一大公子,迟可东处理他的水坝冒了很大风险。当时县里对石清标有所补偿,已经给了一块工业用地让他开发。
“他不能得陇望蜀。”迟可东说。
黄志华说:“人家也没想白拿那片旧厂房,只是希望能有些关照。”
“让他去跟县里谈,我不会为他说。”
“不能稍微点一两句吗?”
迟可东问:“你才回来,不会已经让他给套住了吧?”
黄志华感叹,承认自己有些情况。前些时候他在香港,想回国又怕捕鸟网还支在那儿。找了若干朋友出面帮忙,却还是觉得不踏实。在一个饭局偶遇到香港办事的石清标,两人聊了起来,石清标表示有过硬关系可以帮忙。后来石通过北京的渠道打探情况,据说还找人游说、活动,事情得以明朗。他给黄志华打电话,担保捕鸟网已经卷收入库,不会有问题了。黄志华因此下决心回来。黄志华回来后,石清标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立刻请他吃饭,旧厂房的事情就是在饭桌上提出的。石清标甚至邀请黄志华参股开发,说该地段前景很好,如果黄志华有意东山再起,可以从这里开始。
迟可东说:“志华,安全起见,别跟这个人弄在一起。”
他让黄志华给石清标回话,就说已经把话传给迟可东了,迟可东表示感谢。至于地的事该找谁找谁,他不便出面。
黄志华摇头:“石清标说过,你要是不出面,哪怕他大放血,事情也办不成。”
“那倒未必。”
“他很肯定。”
迟可东说:“不管他怎么说,只能这样。”
“没有余地吗?”
“只能这样。”
黄志华表情落寞,似乎有些失望。而后再不提此事。
其后大约一个月,李金明到市里开会,跑到办公室见迟可东。他跟迟谈起城东新区建设的事情,迟可东即想起石清标所求事项。
“通用厂旧厂房那块地现在怎么样了?”他问。
“还没出手,有几家在谈。”李金明问,“迟书记有什么交代吗?”
迟可东说:“没有。”
那块地的情况迟可东基本清楚。通用厂全称“县通用机械厂”,是县属企业,早年间因经营不善濒临倒闭,开不了工也发不出工资。那时县里搞了个改革方案,把企业的厂房设施及债务打包招商,让一港商兼并重组,工人买断工龄下岗,自谋职业。其间因各种缘故波澜迭起,兼并重组流产,工人利益未得保障,成了一个烂摊子,人称“一裤屎”。那是迟可东从省里下派到县任职之前的事情。迟可东下来后,曾着手收拾残局,所谓“换裤子擦屁股”,经极其困难谈判,与相关港商协议解约,也为该厂下岗职工争取到一些补偿经费,但是仍有众多遗留问题。当年迟可东提出搞城东新区,把该厂厂区划入,一个意图就是解决那些问题。迟可东离任后,城东新区建设成为该县一个重要增长点,通用厂旧厂房渐渐转热,引起开发商注意。李金明在县政府恰分管这一摊。当年炸石清标那道水坝,李金明是城关镇镇长,前线现场指挥,被石清标骂为“土匪镇长”。此刻石清标绝对别想从李金明那里得到哪怕苍蝇大点的便宜,除非迟可东干预。但是迟可东肯定不会干预,尤其是为石清标石老板。彼此间有那么些不愉快往事,如今见面不说分外眼红,也差不到哪儿去。
不料只过了半个月,迟可东给李金明打了一个电话。
“石清标也在竞争通用厂那块地吧?”他直截了当问。
“是。这家伙特别缠。”
“听说你给他找了不少碴儿?”
李金明笑:“他不早说我是土匪吗?”
“你打算怎么着?”
李金明打算把石清标踢出去,不让他来搅和,只要抓住合适的理由,应当可以做到。石老板本事大,别人怕,李金明不怕,早就交过手了。
迟可东说:“算了,别计较以前那些事,还是公平竞争,一碗水端平吧。”
“这可不行。”
“为什么?”
“这家伙财大气粗关系多,说不定就给他弄走了。”
“只要合理合法,该谁就是谁嘛。”
“迟书记的意思是可以让他参加。如果他出的价高,那就给他?”
“对。公平竞争。”
李金明说:“我明白了。”
迟可东没有说自己为什么忽然要替石清标出面,李金明也不多问。对迟可东交办的事情,李金明从来没有二话。
两个月后,李金明向迟可东报告,称通用厂那块地有主了,新主人就是石清标。石清标对这块地志在必得,不惜大放血,终以高出竞争对手一大截的标价拿下。
“我们割了石老板一块肥肉。”李金明快活不已。
迟可东问:“石老板舍得放血割肉,是不是太大方了?”
李金明说:“这家伙一定有他的算盘。”
“你们要留点神。”
李金明说他注意着呢。石清标的事情,不敢不特别小心。那块地确实挺麻烦,关键时候一门横炮“轰隆”过来,几乎把事情打飞。他不予理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迟可东问:“哪来的横炮?”
李金明含糊其词:“也没什么,我能对付。”
事后证明,石清标真不是爱心奉献,自愿为李金明割肉,他肯下狠心确有自己的算盘。算盘算在哪里?在地块的用途上。该地块本属工业用地,必须用于工业开发。石清标也是以工业项目参加竞标,拿下地后却按兵不动,不久即通过省里和北京的关系运作,以城镇化发展、周边功能区变化为由,申请改变该地块属性,将工业用地改为商住用地。该项改动于县里亦属有利,县里愿意支持,同时也提出条件,让石清标负责相关区域道路配套,石清标接受了,因此双方协力报批,最终得以获准。
那个时候就有若干质询声音在本市传播,一直传到市政府会议室里。
有一天市政府开办公会,讨论文化建设议题,与土地开发无关。会议间,市长严海防突然问迟可东:“你那个老地盘有个什么通用厂?”
迟可东告诉严海防,那个厂早在他去之前就倒了,他去时没有厂子,只剩遗体。
“你们拿那遗体卖了个大价钱,是吗?”
“我在的时候没卖成。听说现在他们弄成了。”
“你没听说他们搞什么名堂吧?”
迟可东问:“严市长听到什么情况了?”
严海防称外界有反映,那块地号称卖了大价钱,实际是贱卖,给开发商占了大便宜。这里边是不是有猫腻?是谁干的?经得起查吗?
迟可东说:“反映这么严重,是不是查一查?”
严海防说:“时到花便开。”
果然如其所言,春天到了,树叶就长了出来。此刻李金明已经出事被查。如果外界所传无误,李已承认收受贿赂,他是太不应该。李金明有过教训,当镇长时曾被指控收受旅游开发商郑鑫国贿赂六万元,数额不大,却足以让他身败名裂。当时迟可东认为他虽有失误,并无贪心,设法让他退款过关,自己为之承担责任与风险。如果不是迟可东,李金明头上的帽子早就没有了,他怎么能转眼继续犯错?特别是拿石清标的钱,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蠢?李金明怎么可能不清楚石清标的底细秉性?有过那么一段共同往事,怎么还会如此利令智昏?对迟可东而言,问题在于这笔交易并非仅仅涉及李金明、石清标,与他本人也有关系。一旦李金明寻求减罪,当年迟可东给他打的那个电话足够可用,他只需供称自己是奉迟之命把地给了石清标,就既能开脱若干责任又有立功表现。从传闻看,该情节似已发生,只是因为调查“重要领导”需要权限,让李案办案人员感觉“棘手”。这种“棘手”肯定只是暂时的,案件深查下去,涉及多大人物,就会有拥有多大权限的办案机构介入,时间只在早晚。
迟可东为什么要打那个电话?其原因是否也属“不可告人”?无论如何,此刻这个电话已经进入案件链条,迟可东无可逃避。
——摘自中篇小说《你可以相信》,作者杨少衡,原刊《清明》
阅读全文请关注《小说月报》2017年第8期}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链家代言人 的文章
更多推荐
- ·怎样在美团如何领优惠券上领取优惠券?
- ·外卖代金券怎么领外卖无门槛优惠券?
- ·国际工业制造企业要找仓储服务商,请问金鹰国内前10大国际货运代理公司这家咋样?
- ·我下载的软件注册会员后还能取消吗了终身VIP会员也不能使用,是不是被编了?
- ·人体舒适湿度对照表最舒适的湿度是多少?
- ·漫商汇电商开发商城系统服务包括哪些?
- ·知道的来讲下,这个四个一找房公司的链家代言人人是马琳?
- ·八字流年出现官星是代表正缘出现年份怎么看一定会谈恋爱吗?
- ·求长寿之战里面那首为爱转身插曲是谁唱的歌,歌名是什么,半路停车那首
- ·这首粤语歌词有一句唱着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 ·听说北岳麓书院值不值得进去有个“阅读+”项目,这是做什么的?有哪些特色?
- ·莱斯曼瓷砖是几线品牌陶瓷的光泽度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