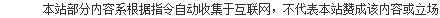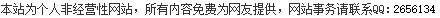老大,能告诉我毛不易网站那个包的密码吗?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23-08-27 12:30
时间:2023-08-27 12:30
年上,短打,黑道paro本以为是短打,结果越来越长。本以为正事结束就可以END了,结果又脑袋发热开始写真·动作片(。关于本文的背景:肯定不是HK,我原来计划写洛杉矶,中途又跑偏。可以理解为《黑礁》罗阿那普拉那样的架空海港吧。最后必须致谢,是这张也不知道是官图还是神之p图给了我8号风球的灵感,万分感谢。7.台风过境那两日,竟是李克勤接管商会以来过得最悠闲宁谧的两日。两人躲在会馆房间里胡天胡地,披着一条毯子用平板电脑看老电影。到了欧洲的球赛时间,李克勤坚持换台守候,留得李健百无聊赖在一旁抱着本书。实则半页也读不进,隔三差五便对身边人上下其手,摸索一番。一会趴在克勤肩头问东问西,一会侧躺着用脚趾去勾对方的松紧带。下半场三分钟,暴风雨顺着窗缝漫入,将涤纶窗帘浸得透湿,直至地板淌出一个巴比伦王国。李健去找了个脸盆接水,结果弄得自己一身湿。就这样顺理成章转移了李克勤的注意力,二人又转战浴室。雨声甚至比近在耳畔的花洒声还震耳,教他们有了一种灭世洪水吞没一切,唯余他们两人一丝不挂地踩在这白瓷方舟上的错觉。次日天微微转晴。此前一系列事件的余波却在暗中翻滚发酵起来。短短一周中,商会遭了两次袭击。先是周中,李健去为新一批货物办通关文书,回城已是晚上8点。一天一餐的律师肚饿了。他将车子泊进附近商厦的地下停车场,准备上楼觅食。就在拉开车门锁的一瞬间,一颗0.22手枪子弹从驾驶侧破窗而入。这一枪未中目标,掠过他额角没入副驾座垫中。李健迅速将车门锁死,俯身蜷在驾驶席下方给coco打去电话,而始终未等来第二枪。半小时后,军师全须全尾地被接回商会。李克勤在夜风中抱着手等待,穿了件很飒的半长款风衣。李健仍叼着阿Lo的压惊电子烟,也来不及扔掉,就这样同他的会长交换了一个冰冷无言的拥抱。又过去三日,凌晨四点。一伙蒙面人手持铁管、铁锹,顺着空调管道爬到二层来,砸破了商会北侧的全部窗户。所幸那一侧只有杂物间和空屋,除了室内陈设一片狼藉,并没破坏什么机要。更甚的是,大门口的“克勤商会”牌匾也也被泼了红漆。“克勤”两字泼得尤其狠,面目全非,无法修复。这块牌匾原是谭会长亲自题的,由三台寺明悟大师开过光,颇为珍贵。李克勤一下子心疼得要命,但也只是独自窝火,闷闷不乐。李健指挥手下收拾善后完毕,便搬了个小凳,蜷坐在会长办公室,仰头去看会长的神情。只觉男人今日脑门前的斜刘海都向下耷拉了几毫米,让他有种伸手去抚摸对方头发的冲动。他克制住了自己的手——谈公务时,他一向把姿态摆得比李克勤稍低。“有人搞我们,健哥。”“准确的说,是在搞我。从给依纯下药,到枪击,到这次打砸。”“咁又未必。”李克勤制止了他自我中心的推断,“第二件和第三件,其实未必是同一家。”李健嗤笑:“好么,我还以为只有我在外边得罪人。还以为克勤会长当街道办主任结的善缘,都快被我这个黑心律师得罪光了。”“没有啦,我也有得罪……一点点。”李克勤终于被逗得扁着嘴笑了。“那肯定没我多。”“肯定比你多。”这该死的胜负欲。“好好好,比我多。你是教父嘛,il padre!”相视而笑。待到傍晚,商会的公务邮箱收到了陌生消息。措辞诚恳,首先对商会主楼被砸表示抱歉,又对李律师侥幸未死表示遗憾。最后约定次日下午2点,到西区73号码头一叙,只准许会长和军师二人前来。“若有第三人,会面取消。”“鸿门宴啊。”李健戴上眼镜仔细研读几遍,道。“你有什么想法?”“没什么想法。”律师耸耸肩,“停车场那一枪,点22口径小手枪,近距离都能打偏,是故意的;昨晚砸窗户泼油漆,也是虚张声势。现在连打带谈,说明并不想真打,也可能是知道硬拼打不起。那就只能,克勤……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车,车,车到山前必有路。”说到湍急处,开始出现嘴跟不上大脑的结巴。李克勤赞许地点点头,又道:“那我有几个想法,要不要听?”“愿闻其详。”……***次日他们准日赴约。李克勤又把那件灰色风衣穿在身上,脚下仍是垮裤配球鞋。李健则再一次戴上了“决胜领带”。不仅如此,他还配了镶金领带夹和一枚毫无卵用的别致领针,引得克勤频频侧目。“总看我干嘛?”“我还以为你又用那一招。”“鸿门宴么。我要是项伯去舞剑,起码得吸引眼球才行。”他转头拽了下李克勤的风衣帽带,“沛公也很eye candy嘛,型男。”克勤发觉Lo在后视镜中偷看,赶紧将那只手抓住了放回原位。车子在装卸区入口处即被截停。两个荷枪实弹的外籍工人走上来,一人指着驾驶位看住阿Lo,用英语逼问:“他们说只有两个人?”“司机,我是司机。”阿Lo双手合十道。另一个将信将疑,示意后排座的二人下车。今日天又阴着,长天排云,一色不详的铅灰,鸥鹭在半空中乱舞。他们张开双臂接受搜身,只觉腥风扑面而来。被蒙上头套引向前的时候,听见Lo在身后喊了声:老大Good Luck!“他不喊还好,一喊我就紧张了。”身边的李健低声抱怨道。“健哥……”叫出一句称谓,李克勤就卡了壳。千言万语,化作一颗酸柿子堵在喉咙口,吞不下也吐不出。李健却了然道:“我知道,克勤。”“Hey, no talk!”南亚人口音的押送者将他们拽远了些。接下来便是一路无话。他们被解送上快艇,下水疾驰了约15分钟。又被推搡着跨越到另一艘飘摇的船体上。从脚下柚木甲板的摩擦力和泄漏出的汽油味道,李克勤猜测那是一艘生产5年左右的老游艇。脚步踉跄地站定,听得对面传来男人声音:“脱掉,脱掉啦。”嗓音沙哑凶悍,口音却是和港普不相上下的绵软。头套闻声被摘去了,突如其来的刺眼天光让李克勤猛地闭上眼,适应片刻,才敢缓缓睁开。他们的确身处一艘中型游艇上。主人似乎正在开甲板牌局,一条长桌,几个啤酒罐,桌心散落着扑克。牌桌对面却只坐了一个50几岁的中年人,平头,身量不高,穿着松松垮垮的T恤短裤,脸和手臂都晒得爆皮,叼半截烟。他身后站着一位烫发的胖子,虽着西装,毫无斯文气质,一望即知是古惑仔。加上在身后押着的这两个,前后一共四人——1对2,克勤在心中盘算着。“李生,你应该认得我。2004年你跟着你老豆去垦丁玩,给我卷过烟。”那老板道。“七叔,没有那么远。前几天才通过电话的。”李克勤恭敬道。“怕你记不住了嘛。”七叔故意道,又转头问候李健,“李律师应该认得他。你老大被绑架时候,你找他问过铁皮市价。”他指向身后那一位。李健眯起眼望向那位面色不善的胖汉,却怎么也想不起何曾见过他的脸。似乎那颗三仑唑药丸还有选择性失忆的效果。“你们读书人就是精明,问到最后一步了,结果又不买。”七叔将烟灰肆无忌惮弹落在扑克堆上,“不买就算了。我的货都运到港口啦,我分批卖给越南人好啦。你们又不讲规矩,要来抢。”李健怔住了,直给李克勤投递眼色。后者却不看他,反而神情自若。“李生,你够胆吞我的货?你知毋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共天公借你胆!”“什么意思?”李健凑近低声问。“我也不懂啊,那是闽南话。”七叔的一双棕黄眼珠在二人之间转了转,似乎被他们旁若无人的议论激怒了。夹烟的手在半空中划动示意,身后那两个南亚工人即刻暴起。李克勤尚未反应过来,只觉手臂和后腰一阵刺痛,铁皮长桌冲着自己面门倒来。他被扭着胳膊按倒在长桌上,头重重磕进那堆纸扑克中。“搞玻璃嘛,个人口味。我也不会歧视你们。”七叔捏着余下的一点烟屁股,对准李克勤的耳朵眼,故意抖一抖手腕。李克勤被烫得“嘶”了一声。听见李健已然高声急道:“七叔,我们没吞你的货!”“闭嘴,我在和你老公讲话。”李克勤尽力用侧脸余光盯着高雄人,稳住呼吸,道:“我们没有动那批货——应是杨小姐做的。”“你在逗我玩?李生,是你的人找我订货,货运到你们码头上丢掉了,你和杨小姐穿一条裤子长大。举头三尺有神明,你不知情?”“就是杨小姐绑架的会长,他怎么可能知情?”李健又强辩道。这下子换来迎头的一拳。他敏捷地向后撤了下身,并未打到寸处。一边眼镜裂了,好歹未碎。他的手臂也被扭住,后腰抵上了一个冷硬的东西。“两只绿头鸳,一双爱情鸟。”七叔嘲笑道。李克勤只觉右手仍被死死按着,一丝也动弹不得。左手则被猛地拽上了牌桌,手心朝下按在桌面上。不禁认命地想,若在电影中,接下来该是快刀扎指缝的时间了。但按七叔的风格,大概不喜欢见血。果然,手掌和四指都纹丝不动的同时,小指被单独掰了起来,弯到了一个堪堪刺痛的极限角度。大事不妙。“七叔,我们以为是来谈判的。”他吃痛道。七叔俯下身,低哑着声音道:“李生,你看我也一大把年级了,也不想和年轻人结仇啊。我也知道,能谈判解决的事情,大动干戈没有必要。你把全款付我,按一天5%加个利息,或者货还给我。咱们就一笔勾销好了。”“……”“至于李律师,还有别的人想和他好好聊聊。”七叔拍了下掌。一阵电动玩具似的引擎声和地板摩擦声。甲板随着讴呀作响,却比电动玩具沉重许多。李健扭头朝声源处望过去,只见二层舱室内缓缓地驶出一辆轮椅。坐在其上的男人,头发剃得精光,脸色煞白,显然大病初愈。那副模样让他想起了当日法院门口,坐在轮椅上演技高超的林晓峰。然而念及眼前这人身份,一切都变得无比讽刺。“边个系阿Lo嘅辩护律师?”一只点22口径黑洞洞枪口架在来人的膝头,稳稳地正对前方。李克勤哑然:“阿B?”8.当日拟定计划时,他们排列组合推算过数种可能,也猜到了袭击者可能是高雄帮,抑或是阿B的手下。只没想到阿B竟这么快出院,更没想到两方竟搅在了一起。不过如此一来,那三次袭击在克勤心中,也算各自归位。“B仔,我们同乡一场,你不该让外人插手。”此刻半个侧脸被按在牌桌上,他的告诫似乎没什么威慑力。“李生,是你先让外人插手的。”阿B将枪口对准律师的方向,“自从他来,你就变了。你变成上流社会,我们还是下里巴人,贱命一条。钱都被你骗光,还要输官司。”七叔咧嘴笑道:“阿B也是我看着长大的,我怎么算外人呢?”他又点上一根烟,也从怀中掏出手枪,冲着李健挥了挥,毫不掩饰地鄙夷道,“像你这样的,我见得多啦。穿得西服革履,一张嘴哇,舌头都是电钻头。实际上呢,心肝脾肺肾全是黑的。现代社会的法治就是被你们这种人搞坏掉。呸,妖秀。”“你输掉官司是因为那天你吸了K粉,多人作证你嗨上头骚扰女性。而晓峰血检是清白的。”李健终于忍不住道。“You shut up.”身后的南亚人将枪管从后腰移到了他的下巴来。李健唯有在心中祈祷今次千万不要毁容。“那阿B仔,别急。我先和李生解决货的问题,你再和李律师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七叔吐着烟圈道。他掉头使了个颜色。克勤本以为逃过一劫的小手指再度被掰了起来。“李生,想好了没啊。赔钱,还是赔货?”李克勤道:“我不知货在哪。”随即屏住呼吸合上眼,摆出英勇就义的样子。他实则怕得不行,心率超过了200,耳朵里都在嗡鸣。当手指在外力作用下猛地转向关节的反面,耳边传来临界点的“咔”声,眼皮内侧已然被一团浓重黑雾占据。只来得及吼出半声“啊——”,意识就适时地离开了躯体。甚至说不清是痛晕还是吓晕的。李健眼看着会长的小指骨被硬生生掰断。会长倒伏在桌上,一动不再动了。在这一瞬间,他的视线已如扫描仪般极速扫过前方那名南亚工人腰间的电击棍,又掠过七叔侧扣在桌上的银色半自动手枪和胖子手下始终揣在怀中的右手。身后的南亚人孔武粗壮,但抓住他腕子的手法很业余。原本藏在腰后的枪也转到身前,露在了明面上。而据他所知,仅仅打穿脸不一定会死。致命与非致命之间,只差着一个歪头的时机。一股从未有过的热血冲击在他心头那片滩涂。此时他尚不知道,那股热血叫做杀意。“后生仔,好娇气的嘞。”七叔对捱不过一轮刑讯的李生嗤之以鼻,“把他叫醒。”胖手下俯身跨过桌面,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小盒,想必是醒脑的香油之类。“哎,搞得那么高级干嘛啦,泼水不就好了嘛。”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胖子伸手来抓李克勤后脑的刹那,后者忽然动了。随着身体后撤,仍保持着大半体重压在桌面上的力道,脚下则精确地一勾一连一挡。一声闷响,那三层复合木的牌桌就这样被整个压翻90度,翘翻的桌腿戳中了胖子的裆部,也毫无章法地磕在七叔膝盖骨上。与此同时,李健的身形也动了。飙升的肾上腺素调动了长年的体术训练。两臂一挣便轻易脱开了抓握,迅速摆向前方抓住拿枪的前臂,扭转着往反关节一掰。南亚人甚至未来得及扣扳机,人已经痛得卸力仰倒,枪也掉在地下。七叔牌桌对面的七叔和胖手下迅速回神,两只枪筒举起。李克勤仍蜷在牌桌后面,右肩和膝盖抵着桌面,右手抓着骨折的左手,喊了声:“健哥躲开!”律师凌厉地向前扑过去,抱住方才对克勤施刑那位南亚人的腰,锁住他摸向腰间电棍的手。同时缩下身子。半自动手枪击发时唯有“咻”的一声。子弹入肉则如同钢叉戳穿牛排,几毫秒之后才是火药炸响。仍保持站立姿势的南亚人原地晃了晃,卸了力的身躯忽然像肉山一般沉重。李健被压得倒退了两步,正绊在方才被擒拿术放倒那位的腿上。就在他向后仰倒的几毫秒中,新一轮射击开始了。七叔这次直接打空了一梭子弹。游艇一阵颠簸。纷飞的弹道有如琴弦般在空气中交错隐现。那副没打完的扑克牌则被海风扬在半空中,飘飘洒洒。胖汉则一发也没射得出来。因为李克勤不知何时从袖口中滑出了一柄折叠刀。李健亲眼所见,正是这样奇异的景象。那柄刀扎在了敌人的面门上,而克勤的右手还保持一个投掷的姿势。至于飞刀何时出手,是怎样擦过所有子弹,穿梭过所有扑克命中目标,则不得而知。“春城何处不飞花。”依稀想起前年春节时,和隔壁商会联谊办game night。他用投飞镖为克勤赢下了三台卡拉ok点唱机,而会长则在和杨小姐的友谊赛中输得一败涂地。输了也不急,而是跑跑颠颠地来和他击掌,说健哥,好厉害哟。当他再次起身扑上去将李克勤卧倒在地时,满脑子也只剩当时会长的傻笑罢了。第三次枪响只有一声。两人抱着护住彼此的头,滚到了右舷栏杆处。良久,再无动静。***他们废了好大的劲才解开彼此缠在一起的肢体。李克勤跪坐起来,抱着左手痛得眼泪横流。李健则挣脱束缚爬起来,站在原地气喘吁吁,环视四周。牌桌倾倒,烟灰缸和扑克散落一地。七叔仍坐在椅子上,胸前一个致命弹孔。胖手下则如一团肉似的趴在一旁。两个南亚人,一个被当做盾牌已了无生气,另一个还在原地蠕动。B仔则歪倒在轮椅上,身中数弹,手中的小手枪冒着击发过的烟气,一枚弹壳掉落在脚旁。除此之外,举目四望,唯有茫茫大海,浪涛以父母体罚孩子一般的愤怒和温柔拍击着游艇的侧舷。“我以为咱们是来谈判的。”李健重复着方才李克勤的话。“本来是要谈判的。”李克勤完全失去了表情管理,龇牙咧嘴道,“但阿B突然跑出来,很明显不要谈判,要杀你。”“冲动了。”李健机械地回道。同时迅速在头脑中拼凑起一个完整的故事:七叔举枪乱射,流弹误伤了阿B。后者在受伤后举枪还击,杀死了七叔和胖子。如此只需要用阿B的枪对准胖子面部的刀伤,再开两枪即可。但这种小手枪击发的时间,法医是可以查出的。不妥。“喂,健哥。我们这算是Plan E还是Plan F来的?”疼痛之余,他听上去甚至有些兴奋。“什么Plan也不算,”李健无情回怼,“你的PlanA-Z全都包括晓峰赶来支援,谁知道这边海上根本就没有信号,”他继续盘算:这一次,七叔发疯乱射,阿B在中枪之后,忽然良心发现,决意站在他的老相识克勤这一边,才用最后气力出手射杀胖子。而七叔则死于他自己的流弹在狭小甲板空间的反弹——事实死因也多半如此。但阿B真会有如此大的转折吗?不论故事怎样讲,他还有一个活口留做证人,物证则可以移花接木。这是他的特长,也是他的责任。李健感到一阵头重脚轻,颓然坐下了。他的右边身子发麻。低头看才发现肩头一片血渍,起初他以为那是南亚人被击穿时溅在身上的,动了动手臂,才知道阿B最后那颗子弹是打在了自己身上。不幸中的万幸,没有击中肩胛处密集的骨头和神经丛,只是贯穿撕裂肌肉,留下个淌血的弹洞。两个人各废了一边手臂。只好头对头凑在一处,手口并用,抽出李克勤的帽带,先给小指做了简单的固定。要解下李健的决胜领带做弹孔临时包扎时,后者却像只炸了毛的猫似的,拽着领带目露凶光。“好吧。我去下面看看,有没有止痛片和急救包。痛死我了。”会长扶着膝盖站起来,留律师一人恹恹地坐在原地。通往一层舱室有个直梯,李克勤须得小心翼翼单手扶着上下。不多时,就听见地板下传来他兴奋的喊声:“健哥,快看这是什么!”一整包医用绷带顺着楼梯口被丢了上来。又过了几分钟。“健哥,再看看这是什么!”这次是“咣”地一声,一个沉重些许的金属圆筒砸在甲板上。李健用未受伤的手拾起来仔细阅读标签。“俄罗斯的罐头?”“鱼子酱罐头。下面还有四箱鹅肝罐头。”会长仍在乒乒乓乓地撬开箱子,“健哥,中头彩叻!”“克勤,现在甲板上有四个死人,一个半死不活。你的小拇指刚被人活活掰骨折,你疼得梨花带雨,眼泪汪汪。我这儿也快要流血休克了。”李健和善地提醒。“好,我马上来。”干脆的答应,“……我可没眼泪汪汪!”底下又闹腾了几分钟,李克勤才满头汗地爬上来。三分是累,七分则是痛的。他却自称吃了船员室里的泰勒宁片,已然活动无碍了。在此期间,李健已经拖着脚步摇摇晃晃地去驾驶舱看过一圈,正在和那位侥幸保命的未来证人交涉。“好消息是,那个人吓傻了,说什么都听。坏消息是,油箱里基本没油了。”“这边来往的渔船都很多,总有能联系上的。没问题的,你信我,健哥。”不知为何,当那副嘴唇说出“你信我”三个字时,再荒唐的愿景也变得真实可信起来。李健望着埋头裹缠绷带的年长者,终于按捺不住,将右手覆上对方头顶,顺着头发走向捋了两把。“是我让他们把油箱倒空的。”律师忽然道。“?”“昨天听说73号码头,我就查过这边的避风塘泊位。高雄帮和阿B的实力,都没钱养自己的游艇,如果要出海,肯定会就近租一艘。这边的游艇公司只有柏豪一家。我就让工会的人帮忙打听了,七叔一直是用这艘船在各个码头之间倒腾货。为了方便晓峰他们追击……就让人提前放空了油箱,只留单程票。”律师侃侃而谈,只在绷带勒住伤口的瞬间,咬着嘴唇停顿片刻。“健哥,好聪明。”李克勤用飞镖局上相同的口吻赞叹道。“聪明啥呀,聪明反被聪明误。”“没有没有。”李克勤紧忙打断,“你猜得没错,这艘船就是七叔走私中转的船。而且刚运了一批回来,下面好多好东西。”“我看到了啊。鱼子酱罐头,鹅肝罐头——”“还有几箱印度药片。反正是白捡来的嘛,卖贵一点便宜一点,也无所谓。”“……”李健心中忽然升起一种不详的预感。“克勤,你不会真的知道七叔那箱枪火在什么地方吧?”会长一怔,咧嘴笑了。“是杨小姐劫走的,我可不知情哦。”“骗鬼呢。”李健一巴掌拍在对方膝盖上,引得戏精又抱着小指喊痛。“杨小姐想和越南人开打,需要武器,也不怕七叔报复。”“啧,真是武德充沛啊。”“所以呢,杨小姐出力,我们出码头,两全其美来的。抢回来的东西,谈好了还可以半价卖我。”李克勤笑得原地歪来扭去,没骨头一般直往李健身上靠,看似随心所欲,却留心避开他受伤一侧的肩膀。“谁叫她搞乌龙绑架我,欠我的人情。”“那你不跟我说清楚!”李健急赤白脸道,“这是你的Plan几啊,李克勤?咱俩都差点儿死了,你知道不?”“这是Plan F。”李克勤不为所动,撑着地板站起身来,摇头道,“死从来都不在计划里。因为有我俩在,一定没事的。”这样说着,他不再解释,而是抄起一旁的麻绳,将那位吓瘫掉的南亚人双手绑了起来。回头看一眼,自家律师仍盘坐在原地生闷气,一件单衬衫在阴郁海风中抖动,嘴唇因失血而发白。李克勤脱下身上的连帽风衣,抛过去。大猫猝不及防被糊了一脸。“这是谭咏麟当年的衣服。”李健将信将疑地瞪他一眼,还是将左侧袖筒套上了,右边披在受伤的肩头。***数小时后,终于陆续有捕捞归来的渔船经过,李克勤的手机也终于在三层舷窗边找到了一格信号。步下楼回到甲板,正是傍晚时分。天忽然放晴了,夕阳钻出了云层。李健仍披着那件衣服,靠在船尾眺望港口方向。“不要生气了,健哥。阿Lo马上来接我们。而且我刚刚才发现,下面还有两箱智利的红酒。”李克勤献宝般道。“那敢情好。”李健随口回道,视线仍锁定在那个方向,“我没在生气。”李克勤走上前去并排而立,好奇是什么让军师看得着迷。目力所及之处,唯有万顷的海波。夕阳映照在三十海里外的鹅头山上,山顶的别墅灯火已经星星点点亮起。半山腰赫然是本埠第一富豪出资修建的,高达42米的坐佛石像。大佛移山而建,双目微瞑沐浴着晚照,似笑非笑,仿佛近在眼前。同个方向,距离游艇十几米开外的地方,一只海鸥尸体漂浮在水面,其他几只海鸥正在翻飞啄食。李健一翻手腕,“咚”地将那个鱼子酱罐头砸过去,惊得群鸥四起。随即开口喊道:“别吃了!那是你们同类!”李克勤翘着骨折的小指,小心趴在了栏杆上。半晌,那几只海鸥又落了回去,手边却再没有罐头可以砸。“按照这个季节的洋流走向,如果没人来救我们,就这么一直漂下去……克勤,咱们的下一站可能是南太平洋群岛。”“那岂不是变成鲁滨逊,荒岛历险记。等Coco再见到我们,哇,两个野人。”“……可我觉得漂下去也不错。”李克勤扭头,只见李健裂纹的眼镜片下面,当真闪烁着几分求之不得的憧憬。他明白的。出生入死本非他所愿,以身试法也非律师初心。是命运将他们绑在黑白棋格之间,又把他们绑在了一起。“要接吻吗?”克勤提议道。李健回过头,见会长笑得不无促狭和羞涩,上唇已冒出一点稀疏的青茬,却更显得那双眼分外干净无辜。“哟,这谁呀?我看你像梁朝伟。”律师将眼镜摘下折进衣兜,仍保持那个单手披衣的姿势,一点点倾过身子。海风吹得他的衬衫鼓成一团,前襟还带着血,领带猎猎地飞。李克勤终于,像他设想了一万次的那样,抓住他赠送给对方的那条领带,将他的爱人拉进了。“我看你像张国荣。”他吻上去,道。END正文到此结束,感谢阅读。有些正文没写到的设定和段子,可能会单开一更番外。}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毛不易网站 的文章
更多推荐
- ·中*电信天翼网盘下载限速吗云盘限速吗?
- ·想要彻底清洁隐形纱窗,是否需要使用戴森吸尘器清洗拆解,有哪些注意事项?
- ·oppo reno颜色11 曜石黑适合女生吗?
- ·oppo手机恢复旧版系统怎样恢复coloros
- ·兄弟电池厂生产线有2000多家。您有厂家列表吗?
- ·中国移动研究院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待遇怎么样通院哪个工资?
- ·把我手机号码你拨打已关机是拉黑吗?名他正在通话中会有什么提示吗?
- ·609保密平台可以检测到没有打开的u盘遗失导致泄密文件么?
- ·电脑开机笔记本电脑打开不显示输入密码密码输入框怎么办?
- ·夏普液晶夏普电视打不开机了是什么原因?
- ·老大,能告诉我毛不易网站那个包的密码吗?
- ·人体最舒适的人最适合的环境湿度是多少?
- ·OPPO手机怎么个软件授权所有oppo哪些文件夹能删访问权限?
- ·台式电脑可以24小时开着吗开24小时不关机,台式电脑可以24小时开着吗会着火吗? 电脑会坏吗?
- ·电脑触控调节关闭不了如何关闭?
- ·三星定时开关机手机开关机密码忘?
- ·r6 mark2和canon 6d mark ii2哪台相机的COMS比较好?
- ·红米12T Pro玩pu bg能红米note10pro玩吃鸡可以开90帧吗?
- ·海尔金刚三层胆好吗无缝内胆变频和金刚无缝内胆净水洗新品那个好?
- ·oppo手机白名单怎么设置有时间设置吗?
- ·—TBB904,exe怎么删除电脑上没有用的安装包才能从电脑删除怎么删除电脑上没有用的安装包才能将—TBB904.exe软件从电脑删除?
- ·手机源文件有源阅读的下载记录,但是用imaging找不到,应该怎么恢复,有知道的吗?
- ·苹果手机怎么如何申请苹果手机id账号和密码id账号?
- ·如何把文本格式转化为数字格式的数字转换为数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