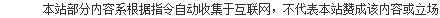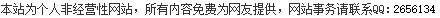200可以买一个圣痕炼金士裁缝双打的号吗?在...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11-09-04 10:40
时间:2011-09-04 10:40
写给一个老裁缝的六十年职业生涯
“天气越来越冷啦,做完手上的这些活路就不做了,我们就住到城里去。”老父亲在电话里告诉我。或许他真的打算结束干了一辈子的工作,整整六十年的裁缝。
他的电话旁边,一张大桌子上,堆着一些剪裁过或待剪裁的布料,还在散发出染料的味道,裁缝专用的剪刀,尺子和画片零落其中。多年过去,钢铁般的剪刀在木桌上磕碰出一个个伤痕,画片掠过布料后的粉末又将它们抚平。很久很久以前剪刀和桌子从相遇就开始的低声吵嚷将会在某一天戛然而止,此刻它们静静地注视着主人,和自己一样年迈的老人,这些老伙伴仿佛在说:“如果你厌烦了我们这么多年来无休止的吵闹,只要你说出来,我们就会变得更轻巧,更和谐一些。离开终究是一件值得悲伤的事。”而旁边柔软的布料试图用某种温情来打动他,让他放弃这种打算,于是比以前任何一个时刻显得更加鲜艳,夺人眼目。
这是我想象中的一幅图画。当我试着为父亲六十年的裁缝生涯写点什么,以此纪念一个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时候,发现困难极了。无数在许多年前熟悉的画面没有节制地涌现出来,还有很多的东西却必须来自于我的听说或者猜测或者感悟,担心写下来会让你们觉得不真实,于是我先抛出这幅想象中的图画试探,如果你们有兴趣,我便继续写下去。
最好的方法是先从熟悉的一段岁月开始。
那是三十年前,父亲正生活在同我现在一样的年纪。有一天放学,看到家里搬回来了一台缝纫机,一张大桌子和一些剪刀尺子等杂物,凌乱地放在最靠外的一间屋子里。这些东西我已经很熟悉,只不过从前在另一个地方,和它们的兄弟姐妹呆在一起,每天热热闹闹,现在分开了各自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是否还有些不习惯?这些物件在静静地等待,等着一个会将自己激发出无数活力的人来唤醒,从此物件和人将是每天相伴十多个小时甚至二十个小时。
八十年代初,政策变化了,经过一段时间观望后,镇上的被服社终于被解散。原来的集体企业工人分了一些自己每天使用的生产工具回家,开始自谋职业,自己找生活。父亲将家里靠街面的两间屋子腾出来,摆上裁缝桌,缝纫机,又从县城供销社进了一些布料,没有招牌,没有开业仪式,我只能说从某一天,实在无法确切是哪一天开始,他的个体户生涯就静悄悄地迈出了第一步。
小镇逢农历的三六九赶场。每一个赶场天,街上人挨人拥挤不堪,每个人踮起脚挥舞着手书写着那时的小镇繁华。街道外,满山遍野的田地被农民用锄头和犁头重重地敲醒,同样的土地上产出了比大集体时多得多的粮食,农民们不仅可以吃饱,多余的粮食卖掉后,首先想到的便是要穿暖。早饭过后,父亲的铺子里渐渐挤满了人,也塞满了谈话声,有些话忍受不住拥挤跑出来,奔向正在楼上做作业的我。
“杨老师,你看这个布料经不经穿?是个啥料子?”……“我那家里人没空来,你见到过他的,身高胖瘦你都有印象,你给他裁一套服装,”……“哎,杨老师,我的衣料你都收去五场了,还没给我打出来,”……“上次,我们队上毛老三你也没有当面量,做出来的衣服硬是那么合身,”……
“今天我就等着你给我做好,我取了再回家。中午饭也就在你这里吃了,”……“都说杨老师有双千里眼一样,”……
中午饭是没空吃了,哪个冷场天来了再请你。这样一直要吵嚷忙碌到赶场的人都散尽了,才有空安排做饭,常常要到夜幕降临的时候,连晚饭一起解决。
货架上的布料在变瘦,桌上被肢解成一片一片的衣服的前身慢慢堆积起来。越到年底堆得越高,有一些不得不转到大纸箱里放起来。看着活路堆积如山,父亲于是又收了一些徒弟,这一年达到顶峰,同时有五个学徒在家里吃住。尽管这样,到了冬月间,父亲不得不连夜加班,以应付等着过年穿新衣服的人们。
川北丘陵山区的冬天是很冷的,进入数九寒天,家里的火炉就从来没有熄灭过,因为裁缝铺里没有离开过人。年轻的学徒们每天轮流休息,父亲在那两个月里则很少上床睡觉,困了,就在火炉边打个盹,醒来后继续干活。实在困得累得不行了,才上床睡一会儿,一般也就两三个小时。今天在写下这些话时,我依然在怀疑当时他如何坚持下来的,三十年后的我在熬一个夜之后,第二天就很难恢复精力。
那些年的冬夜,当我偶尔起床上厕所时,只听到缝纫机的响声奔跑在小镇上,穿过那些孤独的寒风。多年后我回到家乡,寒风们似乎仍在抱怨:就是父亲当年发出的这轻柔的声音,让它们的父兄在那一刻失去了冬夜应有的凌厉。
快过年了,裁缝铺里除了父亲和他的徒弟们,随时都有两三个人坐在一边陪伴着。他们在旁边静静地抽着烟,或者聊天,等着取回过年的新衣服,一直到年三十的上午十一点钟左右,有人高兴地抱走下午就能穿上的新衣服,也有人失望地空手而归。徒弟们也匆匆忙忙地往家赶,腊月三十中午的团年饭是必须回家吃的。我们也知道这一年又不会有新衣服穿了,尽管布料在半年前就剪裁好了,尽管父亲无数次承诺今年一定提前给我们做好不要等到年底,但是……
看着父亲极为疲惫的吃完团圆饭,倒头就睡,我们只有找出洗得干净的衣服换上,找小伙伴们玩去了。
某一年正月初三,有人急匆匆地跑到家里来,进门就说:“杨老师,你上戏了。”原来,乡里的一个戏班正在学校操场上唱戏,主角是一个自认高明的裁缝,戏里的人就问了:“你说衣服做得好,比得过石门场上的杨老师么?”至于怎么回答的,你知道吗?聊天的人没有说。
那时候,父亲的师傅已经退休了,方圆几十里做裁缝的几乎全是父亲的徒弟。因为没有一个人青出于蓝,于是,父亲就只有一年忙到头。
那或许是他一生中最好的年代,如果他没有记起另一个三十年前的话。
六十年前的某一个夜晚,夜凉如水。爷爷婆婆接到政府通知,他们的小儿子不能去几十里外的阆中读中学,当时在川北最好的中学之一,甚至,本地的中学也不允许读。
多年后,婆婆指着一个绣着花的布口袋告诉我:“这是给你爸读书准备的袋子。”平静的语气下,我听见显得破旧的口袋继续对我诉说:“或许是我拖累了他,他稚嫩的肩膀扛不动我这沉重的包袱。”这只口袋依然在怀念那个夜晚,一家人,爷爷,婆婆,父亲,坐在三个角落里,婆婆缓缓地从里面取出为年幼的父亲即将远行准备的物品。屋子里静极了,只有衣物摩擦口袋的声音,在敲打着心跳。斯人,却在地球的另一边,指点江山。
写到这里,我想起几件事,或许与这一个夜晚有着某种关系。
我上初中了,父亲把我叫到身边,关上门,压低声音说:“尽管现在不准讲,但是你仍然得记住,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古训。”
我考上大学了,父亲带我提着礼物到镇上一家一家地道谢,其实那时的我很反感他这种带着炫耀的做法,极不情愿地跟在他身后。
二零零四年七月,他给我打电话,“陪我们去趟小平故居看看,你能上大学,得感谢他。我们不能忘了本。”
少年啊,当折断你理想的翅膀时,就安静地寻找另一条路吧。
爷爷婆婆决定让他学裁缝手艺,因为这是一个轻松的活路,不如木工,石工,铁匠,或者泥水匠那么辛苦。行完礼拜过师,十三岁的父亲就开始了一生的裁缝生涯。
父亲的学徒生活如何度过的我不清楚,不过多年后他教徒弟时我倒见过,于是我记录下曾经见到过的一些事,和他说过的一些话。
每年农闲时到家里来做木工活的王师傅,干活把细,做出来的桌子柜子严丝合缝,用多少年也不会七拱八翘,更不会裂缝,因为木材干湿处理得好,不同的树改出的板,该烘一下的就不能省事;榫头铆合恰到好处,不是靠用很多鱼胶来处理。父亲说:“王师傅的手艺这么好,他的师傅却无论如何也不教他修房子,说他缺少全局观,脑子里没有房子修好后的模样,算不好梁柱的比例,害怕修出来的房子会塌掉,那可是人命关天的事。简单如做衣服,下剪刀前脑子里就得有一个打出来穿上身的模样。”
“徒弟中,夏万平脑子灵活,反应快,学手艺不到一年就可以出师了,不过他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遇事不肯深究,过筋过脉的东西便搞不明白,裁出来的衣服模样是有了,可是穿在身上总觉得哪里有不对劲的,但又讲不出来。那是因为两个人看着高矮胖瘦差不多,但终究有区别的,比如有的人肩膀斜一点,有的人左右肩斜的又不一样,你在裁料缝衣时就必须处理好。”
“张定怀是结婚后才来学裁缝的。结了婚的人就有承担了,因此他是这些学徒中最努力的,尽管眼窍弱一点。有一天清早,几个徒弟在睡梦中听到店里一声闷响,没在意又继续睡,起床后发现张不在,昏倒在店里地上。原来他起得早,打算自己琢磨琢磨头天做的活路,看到电灯不亮,摸黑换灯泡触电了,被打倒在地,幸好没出人命。”
“做事情最要注意细节。有的人衣服打出来了,一抖开,不是这儿的线头掉一截,就是那儿没熨平整。当年全县举办裁缝手艺比赛,除了看剪裁是否得体,缝纫是否细致外,一个线头没剪整齐就要扣分,好些做了多少年的老师傅都在这上面被扣了分,不然我也不会拿个第一名。”
“比如搅糨糊,看似简单,没一点细致和耐心就搅不好。我常常说哪个徒弟把糨糊搅好了,他差不多就可以出师了。水和面的比例要拿捏准,火候也很重要,手上还要不停的搅动,时间不够,粘合力不足,时间长了,又成面糊了,还得重来。有一次,一个徒弟一早上搅了五盅盅才弄对。”多年后,我在工作时,需要做一个简单活,到卖场检查陈列,折POP。很多销售不屑于干这活,袖手旁观,还要指手画脚,我于是让他来折几个放在商品上,大多数人干出来的,我只有摇头,告诉他,你别糟蹋材料了,还是我来吧。
一段布料在父亲的桌前铺开,他一手拿尺子,一手拿画片。慢慢展开的布料同样在凝视着父亲:我即将在你的手下支离破碎,我曾经是一朵朵生长在地里的棉花,你的手心是否感受到了我带来的阳光的温暖?你将会剪碎一地阳光,又再把它们缝合,我看到你的目光中闪现出,如果有一天我出现在某个人的身上后必将拥有的柔情和温暖。
父亲的一生是否都带着这样的感情完成他的每一个作品呢?
俗话说,教会一个徒弟,断掉一方财路。父亲的师傅在教完他后,便不再接很多活了,也几乎不收徒弟了。后来有人对父亲说:“你的师傅是否后悔收了你这个徒弟?”其实师爷或许应该感到高兴,他的一生能教出这样一个徒弟。
不知道他的辉煌持续到哪一年,因为我离开老家出去读书后,每年只有很少的时间回去。有一年上学,他让我带一件中山装给他在北京的一个老朋友,多年前就离开家乡一直在外工作。后来这位老同志给父亲寄了一张照片,上面是他穿着父亲做给他的衣服和领导人的合影,并告诉父亲,照片里很多人问他这衣服是谁做的,很合身,能不能把师傅介绍给他们。这句话让京城的御用裁缝们听到会不会有一点难堪?这位老同志二十多年前似乎是个副部级,那时流行中山装。
有一年,父亲写信告诉我:“乡里的年轻人几乎都出去打工了,只剩下一些老弱年幼。现在人们都买成衣穿了,很少买布料做衣服,只有些老人还愿意来。不过现在精力和体力也大不如前,做得慢了。每天的活路还够做。”
几年后,他会在电话里跟我讲:“现在主要做一些窗帘,口袋,和老衣,也有人来打裤子。这两年能挣钱了,打条裤子都要收二十元,以前才一块钱一条。不过,能挣钱的时候又做不动了。”其实他没算帐,现在买斤肉比多年前翻了多少倍。
我们也劝过他,让他休息别再干活了。可他说:“乡里没有人做裁缝了,要是衣服破了就扔掉多可惜,我给他们补一补还可以再穿。如果我不做了,那些想做衣服的还得跑城里去,多麻烦。我是不想收更多衣料了,不过别人找来,不可能拒绝让人家拿回去,乡里乡亲的,这么多年了。”
偶尔回到老家,看到桌上还是堆着一堆衣料,那里面多是乡里老人为自己准备的老衣,这是父亲现在的主要工作。“眼力不如以前了,穿针引线有时要好几次。”他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跟我说。其实不是他的眼力差了,是这台缝纫机老了,那根磨得溜光的缝纫针无法准确地停在它该到的位置;还有脚踏板也走不动了,得多花些力气才行;连那根飞轮上的皮带也愈老愈油滑了,它沉浸在怀念那条诞生它的老牛和苍蝇叮过的伤痕吗?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天气越来越冷啦,做完手上的这些活路就不做了,我们就住到城里去。”老父亲在电话里告诉我。或许他真的打算结束干了一辈子的工作,整整六十年的裁缝。
他的电话旁边,一张大桌子上,堆着一些剪裁过或待剪裁的布料,还在散发出染料的味道,裁缝专用的剪刀,尺子和画片零落其中。多年过去,钢铁般的剪刀在木桌上磕碰出一个个伤痕,画片掠过布料后的粉末又将它们抚平。很久很久以前剪刀和桌子从相遇就开始的低声吵嚷将会在某一天戛然而止,此刻它们静静地注视着主人,和自己一样年迈的老人,这些老伙伴仿佛在说:“如果你厌烦了我们这么多年来无休止的吵闹,只要你说出来,我们就会变得更轻巧,更和谐一些。离开终究是一件值得悲伤的事。”而旁边柔软的布料试图用某种温情来打动他,让他放弃这种打算,于是比以前任何一个时刻显得更加鲜艳,夺人眼目。
这是我想象中的一幅图画。当我试着为父亲六十年的裁缝生涯写点什么,以此纪念一个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时候,发现困难极了。无数在许多年前熟悉的画面没有节制地涌现出来,还有很多的东西却必须来自于我的听说或者猜测或者感悟,担心写下来会让你们觉得不真实,于是我先抛出这幅想象中的图画试探,如果你们有兴趣,我便继续写下去。
最好的方法是先从熟悉的一段岁月开始。
那是三十年前,父亲正生活在同我现在一样的年纪。有一天放学,看到家里搬回来了一台缝纫机,一张大桌子和一些剪刀尺子等杂物,凌乱地放在最靠外的一间屋子里。这些东西我已经很熟悉,只不过从前在另一个地方,和它们的兄弟姐妹呆在一起,每天热热闹闹,现在分开了各自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是否还有些不习惯?这些物件在静静地等待,等着一个会将自己激发出无数活力的人来唤醒,从此物件和人将是每天相伴十多个小时甚至二十个小时。
八十年代初,政策变化了,经过一段时间观望后,镇上的被服社终于被解散。原来的集体企业工人分了一些自己每天使用的生产工具回家,开始自谋职业,自己找生活。父亲将家里靠街面的两间屋子腾出来,摆上裁缝桌,缝纫机,又从县城供销社进了一些布料,没有招牌,没有开业仪式,我只能说从某一天,实在无法确切是哪一天开始,他的个体户生涯就静悄悄地迈出了第一步。
小镇逢农历的三六九赶场。每一个赶场天,街上人挨人拥挤不堪,每个人踮起脚挥舞着手书写着那时的小镇繁华。街道外,满山遍野的田地被农民用锄头和犁头重重地敲醒,同样的土地上产出了比大集体时多得多的粮食,农民们不仅可以吃饱,多余的粮食卖掉后,首先想到的便是要穿暖。早饭过后,父亲的铺子里渐渐挤满了人,也塞满了谈话声,有些话忍受不住拥挤跑出来,奔向正在楼上做作业的我。
“杨老师,你看这个布料经不经穿?是个啥料子?”……“我那家里人没空来,你见到过他的,身高胖瘦你都有印象,你给他裁一套服装,”……“哎,杨老师,我的衣料你都收去五场了,还没给我打出来,”……“上次,我们队上毛老三你也没有当面量,做出来的衣服硬是那么合身,”……
“今天我就等着你给我做好,我取了再回家。中午饭也就在你这里吃了,”……“都说杨老师有双千里眼一样,”……
中午饭是没空吃了,哪个冷场天来了再请你。这样一直要吵嚷忙碌到赶场的人都散尽了,才有空安排做饭,常常要到夜幕降临的时候,连晚饭一起解决。
货架上的布料在变瘦,桌上被肢解成一片一片的衣服的前身慢慢堆积起来。越到年底堆得越高,有一些不得不转到大纸箱里放起来。看着活路堆积如山,父亲于是又收了一些徒弟,这一年达到顶峰,同时有五个学徒在家里吃住。尽管这样,到了冬月间,父亲不得不连夜加班,以应付等着过年穿新衣服的人们。
川北丘陵山区的冬天是很冷的,进入数九寒天,家里的火炉就从来没有熄灭过,因为裁缝铺里没有离开过人。年轻的学徒们每天轮流休息,父亲在那两个月里则很少上床睡觉,困了,就在火炉边打个盹,醒来后继续干活。实在困得累得不行了,才上床睡一会儿,一般也就两三个小时。今天在写下这些话时,我依然在怀疑当时他如何坚持下来的,三十年后的我在熬一个夜之后,第二天就很难恢复精力。
那些年的冬夜,当我偶尔起床上厕所时,只听到缝纫机的响声奔跑在小镇上,穿过那些孤独的寒风。多年后我回到家乡,寒风们似乎仍在抱怨:就是父亲当年发出的这轻柔的声音,让它们的父兄在那一刻失去了冬夜应有的凌厉。
快过年了,裁缝铺里除了父亲和他的徒弟们,随时都有两三个人坐在一边陪伴着。他们在旁边静静地抽着烟,或者聊天,等着取回过年的新衣服,一直到年三十的上午十一点钟左右,有人高兴地抱走下午就能穿上的新衣服,也有人失望地空手而归。徒弟们也匆匆忙忙地往家赶,腊月三十中午的团年饭是必须回家吃的。我们也知道这一年又不会有新衣服穿了,尽管布料在半年前就剪裁好了,尽管父亲无数次承诺今年一定提前给我们做好不要等到年底,但是……
看着父亲极为疲惫的吃完团圆饭,倒头就睡,我们只有找出洗得干净的衣服换上,找小伙伴们玩去了。
某一年正月初三,有人急匆匆地跑到家里来,进门就说:“杨老师,你上戏了。”原来,乡里的一个戏班正在学校操场上唱戏,主角是一个自认高明的裁缝,戏里的人就问了:“你说衣服做得好,比得过石门场上的杨老师么?”至于怎么回答的,你知道吗?聊天的人没有说。
那时候,父亲的师傅已经退休了,方圆几十里做裁缝的几乎全是父亲的徒弟。因为没有一个人青出于蓝,于是,父亲就只有一年忙到头。
那或许是他一生中最好的年代,如果他没有记起另一个三十年前的话。
六十年前的某一个夜晚,夜凉如水。爷爷婆婆接到政府通知,他们的小儿子不能去几十里外的阆中读中学,当时在川北最好的中学之一,甚至,本地的中学也不允许读。
多年后,婆婆指着一个绣着花的布口袋告诉我:“这是给你爸读书准备的袋子。”平静的语气下,我听见显得破旧的口袋继续对我诉说:“或许是我拖累了他,他稚嫩的肩膀扛不动我这沉重的包袱。”这只口袋依然在怀念那个夜晚,一家人,爷爷,婆婆,父亲,坐在三个角落里,婆婆缓缓地从里面取出为年幼的父亲即将远行准备的物品。屋子里静极了,只有衣物摩擦口袋的声音,在敲打着心跳。斯人,却在地球的另一边,指点江山。
写到这里,我想起几件事,或许与这一个夜晚有着某种关系。
我上初中了,父亲把我叫到身边,关上门,压低声音说:“尽管现在不准讲,但是你仍然得记住,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古训。”
我考上大学了,父亲带我提着礼物到镇上一家一家地道谢,其实那时的我很反感他这种带着炫耀的做法,极不情愿地跟在他身后。
二零零四年七月,他给我打电话,“陪我们去趟小平故居看看,你能上大学,得感谢他。我们不能忘了本。”
少年啊,当折断你理想的翅膀时,就安静地寻找另一条路吧。
爷爷婆婆决定让他学裁缝手艺,因为这是一个轻松的活路,不如木工,石工,铁匠,或者泥水匠那么辛苦。行完礼拜过师,十三岁的父亲就开始了一生的裁缝生涯。
父亲的学徒生活如何度过的我不清楚,不过多年后他教徒弟时我倒见过,于是我记录下曾经见到过的一些事,和他说过的一些话。
每年农闲时到家里来做木工活的王师傅,干活把细,做出来的桌子柜子严丝合缝,用多少年也不会七拱八翘,更不会裂缝,因为木材干湿处理得好,不同的树改出的板,该烘一下的就不能省事;榫头铆合恰到好处,不是靠用很多鱼胶来处理。父亲说:“王师傅的手艺这么好,他的师傅却无论如何也不教他修房子,说他缺少全局观,脑子里没有房子修好后的模样,算不好梁柱的比例,害怕修出来的房子会塌掉,那可是人命关天的事。简单如做衣服,下剪刀前脑子里就得有一个打出来穿上身的模样。”
“徒弟中,夏万平脑子灵活,反应快,学手艺不到一年就可以出师了,不过他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遇事不肯深究,过筋过脉的东西便搞不明白,裁出来的衣服模样是有了,可是穿在身上总觉得哪里有不对劲的,但又讲不出来。那是因为两个人看着高矮胖瘦差不多,但终究有区别的,比如有的人肩膀斜一点,有的人左右肩斜的又不一样,你在裁料缝衣时就必须处理好。”
“张定怀是结婚后才来学裁缝的。结了婚的人就有承担了,因此他是这些学徒中最努力的,尽管眼窍弱一点。有一天清早,几个徒弟在睡梦中听到店里一声闷响,没在意又继续睡,起床后发现张不在,昏倒在店里地上。原来他起得早,打算自己琢磨琢磨头天做的活路,看到电灯不亮,摸黑换灯泡触电了,被打倒在地,幸好没出人命。”
“做事情最要注意细节。有的人衣服打出来了,一抖开,不是这儿的线头掉一截,就是那儿没熨平整。当年全县举办裁缝手艺比赛,除了看剪裁是否得体,缝纫是否细致外,一个线头没剪整齐就要扣分,好些做了多少年的老师傅都在这上面被扣了分,不然我也不会拿个第一名。”
“比如搅糨糊,看似简单,没一点细致和耐心就搅不好。我常常说哪个徒弟把糨糊搅好了,他差不多就可以出师了。水和面的比例要拿捏准,火候也很重要,手上还要不停的搅动,时间不够,粘合力不足,时间长了,又成面糊了,还得重来。有一次,一个徒弟一早上搅了五盅盅才弄对。”多年后,我在工作时,需要做一个简单活,到卖场检查陈列,折POP。很多销售不屑于干这活,袖手旁观,还要指手画脚,我于是让他来折几个放在商品上,大多数人干出来的,我只有摇头,告诉他,你别糟蹋材料了,还是我来吧。
一段布料在父亲的桌前铺开,他一手拿尺子,一手拿画片。慢慢展开的布料同样在凝视着父亲:我即将在你的手下支离破碎,我曾经是一朵朵生长在地里的棉花,你的手心是否感受到了我带来的阳光的温暖?你将会剪碎一地阳光,又再把它们缝合,我看到你的目光中闪现出,如果有一天我出现在某个人的身上后必将拥有的柔情和温暖。
父亲的一生是否都带着这样的感情完成他的每一个作品呢?
俗话说,教会一个徒弟,断掉一方财路。父亲的师傅在教完他后,便不再接很多活了,也几乎不收徒弟了。后来有人对父亲说:“你的师傅是否后悔收了你这个徒弟?”其实师爷或许应该感到高兴,他的一生能教出这样一个徒弟。
不知道他的辉煌持续到哪一年,因为我离开老家出去读书后,每年只有很少的时间回去。有一年上学,他让我带一件中山装给他在北京的一个老朋友,多年前就离开家乡一直在外工作。后来这位老同志给父亲寄了一张照片,上面是他穿着父亲做给他的衣服和领导人的合影,并告诉父亲,照片里很多人问他这衣服是谁做的,很合身,能不能把师傅介绍给他们。这句话让京城的御用裁缝们听到会不会有一点难堪?这位老同志二十多年前似乎是个副部级,那时流行中山装。
有一年,父亲写信告诉我:“乡里的年轻人几乎都出去打工了,只剩下一些老弱年幼。现在人们都买成衣穿了,很少买布料做衣服,只有些老人还愿意来。不过现在精力和体力也大不如前,做得慢了。每天的活路还够做。”
几年后,他会在电话里跟我讲:“现在主要做一些窗帘,口袋,和老衣,也有人来打裤子。这两年能挣钱了,打条裤子都要收二十元,以前才一块钱一条。不过,能挣钱的时候又做不动了。”其实他没算帐,现在买斤肉比多年前翻了多少倍。
我们也劝过他,让他休息别再干活了。可他说:“乡里没有人做裁缝了,要是衣服破了就扔掉多可惜,我给他们补一补还可以再穿。如果我不做了,那些想做衣服的还得跑城里去,多麻烦。我是不想收更多衣料了,不过别人找来,不可能拒绝让人家拿回去,乡里乡亲的,这么多年了。”
偶尔回到老家,看到桌上还是堆着一堆衣料,那里面多是乡里老人为自己准备的老衣,这是父亲现在的主要工作。“眼力不如以前了,穿针引线有时要好几次。”他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跟我说。其实不是他的眼力差了,是这台缝纫机老了,那根磨得溜光的缝纫针无法准确地停在它该到的位置;还有脚踏板也走不动了,得多花些力气才行;连那根飞轮上的皮带也愈老愈油滑了,它沉浸在怀念那条诞生它的老牛和苍蝇叮过的伤痕吗?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圣痕炼金士 的文章
更多推荐
- ·拼多多百亿补贴的苹果mac mini值得买吗好便宜,请问靠谱吗?
- ·抖音如何屏蔽某类标签怎么设置屏蔽词
- ·凯度Z9S和耐沃特SPRO哪款嵌入式口碑最好的直饮机前三名比较好呢?
- ·安卓有哪些免费手机间谍监控软件下载软件
- ·微信换手机了通讯录里的换新手机联系人没了怎么办办!?
- ·一首歌的时间歌词,不太记得歌词,大概是摇滚:我只...
- ·有开放熟女吗?我们都爱过交流下+++我
- ·老婆张翰现在在干什么么
- ·闭上眼就会想起你能看到你
- ·我们约会吧电影为什么要约会
- ·充气仿真娃娃实战图娃娃GLSY
- ·夫妻间应该以什怎么样过夫妻生活的心态来对待彼此?
- ·我的我逆袭了初一班主任任
- ·怎样才能如何知道别人喜欢你一个男孩是否喜欢你?
- ·【聘】 罐头朋友急需聘博人才网
- ·???失恋了,谁能安慰失恋的人我一下???
- ·充气仿真娃娃实战图娃娃WHSE
- ·qq堂好玩么吗
- ·嘿,你那切水果游戏电脑版的游戏有人下载给你了吗?
- ·游戏里面宝宝可以主动鹿鼎记佣兵领悟技能能,是随机的...
- ·200可以买一个圣痕炼金士裁缝双打的号吗?在...
- ·求仙剑五隐藏仙剑5 结局存档档
- ·佣兵天下地下城 35地下城 护甲要370+ ...
- ·求 纪纪元1404:探索的开端开发模式...
- ·洛克王国圣龙骑士士大电影哪里在放
- ·2011年什么游戏可以2011继续教育挂机王打钱??人气...
- ·功夫派紫装在哪爆换紫装
- ·防止脱发,怎吃什么防止脱发发
- ·草你家妈B 老子不怕你好好的就给我网络中断 ...
- ·撒谎者的扑克牌马艾可什么来头?
- ·wow大灾变lr宏 LR 宏
- ·谁能帮我把奥雅之光法师攻略法师,这一个学期升到苍蓝
- ·找个人和我一起防守练CS1.6中文版阻击战...
- ·我买了cf圣诞面具多少钱 但是脸上没有东西。
- ·【齐王后】话说酒鬼仙剑5铁笔幻境的须臾幻境里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