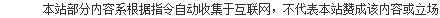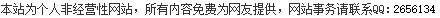爱的反体字怎么写反性书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11-05-23 07:49
时间:2011-05-23 07:49
李翱《复性书》
&|&&|&&|&&|&&|&&|&&|&&|&&|&&|&
您现在的位置:&&>>&&>>&&>>&&>>&正文
李翱《复性书》
作者:佚名&&&&文章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更新时间:&&&&
&&&热&&&&&
【字体: 】
李翱(772―841),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北)人,唐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幼时“勤于儒学,博雅好古,为文尚气质,”后从韩愈学古文。中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进士。曾任国子博士、知制诰,中书舍人,史馆修撰、谏议大夫、刑部侍郎、山南东道节度使等职。为人“性刚急,议论无所避,执政虽重其学,而恶其^讦,故久次不迁”。在仕途上很不得志。武宗会昌年间卒,谥曰“文”,后人将其著述汇集成《李文公集》18卷,并曾与韩愈合著《论语笔解》2卷等。
李翱本人的社会地位不很高,一生的从政生活也不顺利,只是因为在学术上颇有造诣,故受到朝廷重臣李景俭、裴度等人的重视。在政治上和学术思想上,李翱均与韩愈相近。他虽不满于豪强的土地兼并。但却指责王叔文等人的变法改革使“天下懔懔”。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他一生“敏于学而好于文”,在学术上很快成为韩愈推行“古文运动”的得力助手。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韩愈从董晋到汴州,李翱恰好也到汴州来,二人相识后便时常研讨学问。从此,李翱依附韩愈,研究和宣扬韩愈的思想,并娶韩愈从兄韩 之女为妻,二人关系极为密切。他赞扬韩愈说:“我友韩愈非兹世之文,古之文也;非兹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词与其意适,则孟轲既没,亦不见有过于斯者。”韩愈对李翱很是器重,不仅时常通过书信研讨问题,还称赞李翱思想颇为精细,他说:“习之可谓究极圣人之奥矣。”
对于佛教的态度,李翱即不同于韩愈,也不同于柳宗元。作为韩愈的学生和密友,李翱也力主排佛,他著《去佛斋》一文表明反佛的立场和理由,但批评韩愈虽然反佛,而“不知(佛教)心,虽辨而当,不能使其徒无哗而劝来者。”他不赞同柳宗元明确打出援佛入儒的旗号,认为柳氏只重取佛而没有强调维护儒学的统治地位。李翱采取的方法是坚守儒学的立场,明确提出反佛的主张,暗自分析和吸收佛学的思想和方法,为儒学的改造和完善,为儒学最终战胜佛教的目的奋斗。他的这一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韩愈、柳宗元对待佛教思想的偏差,为儒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宋明理学就是沿着这一道路发展和逐渐成熟的。
后人评论李翱,常用“儒表佛里”一词概括之,这的确形象地说明了李翱思想的一个特点,即李翱在思想上受到佛学的很大影响,吸收了佛学的许多主要的思想和方法。早年他曾与信奉天台宗的著名学者梁肃有交往,深得梁肃的赏识。后在任郎州刺史时,与禅宗僧人惟俨时有交往,并常向其质疑问道。他称赞佛徒养心离欲的修身方法和不为外物侵乱的治学之道。他常说;“天下之人,以佛理证心者寡矣。”又说“佛法论心术则不异于中土,考教迹则有蠹于生灵。”肯定了佛教的主要思想内容,抨击了佛教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对佛教的分析是具体的,深入的。他的代表作《复性书》,其基本思想主要来自佛教的《大乘起信论》和《圆觉经》等,受到梁肃乃至湛然等人的熏陶和影响。但是,“儒表佛里”说又不能十分贴切地表现李翱思想的特点,因为李翱虽然吸收了佛教的思想和方法,但终极目标是援佛入儒,改造儒学,最终战胜佛教。所以“佛里”只能解释为包含和兼容,“儒表”则表现出他旗帜鲜明。
在哲学思想上,李翱的主要观点均集中于《复性书》三篇之中。他以性情为主题,以儒家的经典《中庸》为核心,以佛教思想作补充,试图建立起一种新的人性哲学体系,在思想的深度上远远超过了他的师友韩愈,开宋明理学、特别是“二程”思想之先诃。
和韩愈一样,为了发展儒学,与佛道抗衡,李翱也提出了儒家的道统思想,所不问的是李翱建立的儒家道统是以《中庸》的传授为中心的。他说,“子思,仲尼之孙,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传于孟轲。轲曰:‘我四十不动心;轲之门人达者公孙丑、万章之徒盖传之矣。遭秦灭书,《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于是此道废缺,其教授者唯节行、文章、章句、威仪、击剑之术相师焉,性命之源则吾弗能知其所传矣。道之极于剥也必复,吾岂复之时邪?”他制造了《中庸》原有四十七篇的故事,试图以独得《中庸》义蕴的身份占据直承思孟学派思想和儒学正统传人的地位,这无疑是韩愈《原道》思想的故技重演。所不同的是,李翱在论述中引入了佛教禅宗“以心相传”的说法,为“新”道统说和其自身传道者的地位涂抹了神秘的色彩。他说:“有问于我,我以吾心所知而传焉,遂书于书,以开诚明之源,而缺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于时,命曰《复性书》,以理其心,以传乎其人。乌戏!夫子复生,不废吾言矣。”表明他振兴和发扬儒学的使命感和与儒家古圣贤心通神往的特殊关系,为其学说的弘扬制造神话效果。
在《复性书》的开端,李翱明确地写道:“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所匿矣,非性之过也;七者循环而交来,故性不能充也。”在《论语笔解》中李翱又说:“‘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此性命之说极矣,学者罕明其归。今二义相戾,当以《易》理明之。“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又‘贞利者,情性也,’又‘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谓人性本近于静,及其动感外物,有正有邪。动而止,则为上智;动而焉,则为下愚。寂然不动,则情性两忘矣,虽圣人有所难知。故仲尼称颜回‘不言如愚,退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盖坐忘遗照,不习如愚,在卦为复,天地之心邃矣。亚圣而下,性习近远,智愚万殊……。”引用了道家,儒家和佛教的不少内容和术语,不仅将“阴阳”、“道”、“善”、“性”联系起来,还以“静”、“动”作为形成正邪、善恶、上智、下愚的关键。在董仲舒、韩愈“性三品”思想与柳宗元“失性”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性善情恶理论,创造出新的人性思想。
李翱的性情理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导入了佛学的内容,其所言“性”,相当于禅宗的所谓“佛性”,“情”相当于掸宗所谓的“五阴”或“妄念”。《六祖坛经》指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阴持入经注》则指出:“身有六情,情有五阴。”李翱认为这些理论都是可取的,“百骸之中有心焉,与圣人无异也。”并进一步仿照《孟子》一书的笔法写道:“问曰:‘凡人之性犹圣人之性欤?’曰:‘桀纣之性犹尧舜之性也,其所以不G其性者,嗜欲好恶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不为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为也,情有善不善,而性无不善焉’。”在他看来,“性”、“情”是皆然对立的,“性”是善而且万众一致的,不仅尧舜与桀纣同,而且“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也”。“性者,天之命也”。这种天生的善性,就是仁义礼智等德性。而“情”是导致不善的根源,“情者性之动也”,“情者性之邪也”,“情者妄也、邪也”。只有在日常生活中克制和去掉情欲,才能使失去的善性复归。
当然,李翱并不是简单地主张去情存性,而是进一步分析性与情两者的关系。他认为,情虽恶、性虽善,但二者有一种互相连带的密切关系。“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情由性而生,性由情而显,性是内在的,情是外露的,二者互为表里。他进一步比喻说:“水之浑也其流不清,火之烟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过也,沙不浑流斯清矣,烟不郁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情与性不相无也。”因此,欲善不欲恶者,应该努力“复性”、“尽性”,加强修炼以达圣贤之域。他指出:“性者,天之命也,圣人得之而不惑者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也。圣人者,岂其无情邪?圣人者,寂然不动,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参乎天地,变化合乎阴阳,虽有情也,未尝有情也。”只有保持寂然不为外物所动,才能完成“复性”的过程,成为圣贤。由此可见,李翱的复性说是一种抽象的自我修炼理论,具有相当浓重的神秘色彩。他明确地把复性的过程称作“斋戒”,以佛教的修炼养性过程取代儒家传统的修身过程,并把“至诚”作为寂然不动的标准提出来,将佛教的修持方法和觉悟过程与传统儒家的“诚意、正心”思想联系了起来。他指出:“情之动弗息,则不能复其性而烛天地、为不极之明。故圣人者,人之先觉者也,觉则明,否则惑,惑则昏。……夫明者所以对昏,昏既灭则明亦不立矣。是故诚者圣人性之也。寂然不动,广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上语默,无不处于极也。复其性者,贤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则能归其源矣。”“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诚之明也。”只有达到心寂不动,去掉邪思,才能防止昏惑,达到诚明的境地,悟出本性,成为圣贤。
值得注意的是,李翱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对《大学》里的“格物致知”作了一番重要的解释。在《大学》的“八条目”中,韩愈曾舍去了“格物、致知”,将“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李翱在韩愈思想的基础上把对《大学》的分析又推进了一步,将传统儒学中学习成圣过程的理论抬到了哲学的高度。《大学》曰:“致知在格物”李翱解释道:“物者,万物也;格者,来也,至也。物至之时,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应于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诚,意诚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理,国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参天地者也。”他把“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的道德修养过程联系起来,将认识论的问题也纳入了儒家道德伦理的轨道。李翱的这一作法对韩愈的恩想作了重要的补充,并成为后世理学思想的重要特征。李翱所说的“格物致知”非是通过感官去体察体验外物而获得真知,而是以自己的“昭昭之心”去接触外物,锻炼自己,完善自身,作到不为外物所迷,不为外物所迁,却明于万事万物,达到“自诚明”的境界。他的“格物致知”思想完全是以前面提到的“性善情恶”说为基础,甚至可以说就是人性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自《大学》问世以来,重视“格物,致知”的重要论著,说明隋唐儒学逐渐从一般道德伦理之学转向伦理哲学,建立和健全了道德伦理的修养程序。简而言之,李翱的哲学思想是范围较窄的,主要局限于人性思想,其教育思想便是由此而生发出来的。对比韩愈,李翱的思想和实践活动不太广泛,但在哲学思辨方面却胜过韩愈一筹,特别在人性问题上,李翱为性善情恶说,兼容儒佛的理论,为宋代理学“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和韩愈的卫道思想相同,李翱也立志坚守儒学的基本立场,培养合乎儒家道德伦理和理想的君子圣贤。他明确指出:“吾之道,学孔子者也。”“是古圣人所由之道”。并认为办教育的根本目的在教人从儒家仁义之道,而非像世俗之人一样,学些文辞,“以抄集为科第之资”。“吾所以不协于时,而学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故学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礼。”和韩愈一样,在推行古文运动的同时,宣扬古代儒家的仁义之道,遵行儒家的礼制。不仅要“学其言”,还要“行其行”,“重其道”,完成读书成圣的主要教育目的。他曾强调,读书求学是为了“学圣人之道而和其心”。他在劝勉兄弟时曾指出:“仲尼、盂轲没千余岁矣。吾不及见其人,能知其圣且贤者,以吾读其辞而得之者也。后来者不可期,安知其读吾辞者,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其所谓的“心之所存”,即是“圣人之道”,是从读前人之书获得。
因此在受教育,养成高尚人格的过程中,读圣贤之书是重要的和基本的途径。
从人性论的角度出发,李翱认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在“复性”。这和孟子教育的途径是“求本心”、“求诸已”一脉相承,也和佛教禅宗“明心见性”、“直指人心”和“见性成佛”的思想同出一辙,在他看来,世人皆有天然的善性,只因为妄情所惑,通过教育可以使“妄情灭息,本性自明”。故圣人“教人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也。”很明显,李翱的这一主张对理学“存理灭欲”教育思想有直接的影响作用,他从另一个角度补充和深化了儒家传统的教育思想。
为了达到“重道”和“复性”的教育目的,李翱认为首先要研读儒家的核心著作,掌握儒家思想的精髓。他和韩愈曾合著《论语笔解》并特别推崇《孟子》一书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在治学论道中以这四部儒家经典为主。这是后学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儒学最基本教材――《四书》的源头之一。虽然,到唐末,皮日休力主以《孟子》为官学教科书而没有实行,但韩、李二人所作的努力对后世是有极大影响力的,对儒家教材从《五经》转入《四书》,由繁变简,由难到易作出贡献,为儒学与佛道争夺民众,保持正统地位创造了条件。
除了读圣贤书而外,李翱认为应该注重修养的功夫。首先,为人处世应该不为外物所惑,在“无虑无思”中求得“心寂不动,邪思自息,”达到“诚明”的境地,做到“情性两忘”。其次,要努力作到“慎独”,即在不断变化的外界影响下,能够格守本性。他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G,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说者曰;不G之G,见莫大焉,不闻之闻,闻莫甚焉。其心一动是不G之G,不闻之闻也。其复之也远矣。故君子慎其独。慎其独者,守其中也。”第三,李翱认为“复性”的过程是无止境的,因此,“择善而执之者”应该本着“至诚”的精神,“终岁不违”圣贤之道。他说:“复其性者,贤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能归其源矣。”当有人问他“如生之言,修之一日则可以至于圣人乎”?他回答说:“十年扰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谓以一杯而求一车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诚,诚而不息必明,明与诚终岁不违,则能终身矣。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则可希于是矣。”只有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真正达到“复性”的境地。第四,李翱认为在“复性”的过程中,人的主观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指出:“嚣然不复,其性惑矣哉。道其心弗可以庶几于圣人者,自弃其性者也。终亦亡矣,茫茫乎其将何所知。冉求非不足乎力者也,画而止,进而不止者,颜子哉。”只有像颜回那样甘于安贫乐道,才能成为“复性”之人,进入圣贤之列。
在所有教育中,李翱认为对于百姓的教育是最应受到重视的,应该主要针对基层乃至家庭中的主要成员,施之以相应的教育。如“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在乡党使之敬让。”如此,“与之居则乐而有礼,与之守则人皆固其业。”如百姓皆能安分守己,慈孝礼让,则可使天下太平,儒道畅行,人性复归,长治久安。
总之,李翱在《复性书》中从“道”和“性”两个方面突出了教育的目的和作用,其所用概念与韩愈大致相同,但其内涵则更为广泛和深刻。他所要培养的圣贤儒士已非完全是传统儒家的理想人物,已更多地增添了佛教的色彩,在儒学统合佛道,改造自身的过程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李翱的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中,儒佛的思想、观点和方法是杂揉在一起的。他虽然自称“择《中庸》之蹈难兮,虽困顿而不改其所为。”将《中庸》作为自己的思想核心,坚守不移。但却在人性论、教育论、儒家道统等方面对传统儒学作了重大的改革。成为隋唐儒学向宋明理学过渡时期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中唐以后最有创造性的教育思想家,独得儒、佛两家学说之奥。只有认真研究李翱的思想学说,才能促进隋唐教育思想的深入分析,为宋代理学的发展寻求思想和学术的源泉。
(程方平)
文章录入:李明刚&&&&责任编辑:李明刚&
上一篇文章: 下一篇文章:
【】【】【】【】【】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党湾一小 ┋ 书记:曹传虎 ┋ 电话:8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党湾镇卫东桥旁 ┋& 网站备案: ┋&& 网站设计:
Copyright &
All Rights Reserved&最佳分辨率
适用于 IE6.0 以上 下载
 收藏
该文档贡献者很忙,什么也没留下。
 下载此文档
正在努力加载中...
李翱《复性书》心性思想研究
下载积分:2999
内容提示:
文档格式:PDF|
浏览次数:24|
上传日期: 05:19:34|
文档星级:
该用户还上传了这些文档
下载文档:李翱《复性书》心性思想研究.PDF
官方公共微信氧化性,还原性书上说,“同一氧化剂不同还原剂,所需反应条件越低,表明还原剂的还原性越强.”如,2KMNO4+16HCl=2KCl+2MnCl2+5Cl2加热 MnO2+4HCl======MnCl2+Cl2+2H2O是加热,还是所需还原剂的粒子数?_百度作业帮
氧化性,还原性书上说,“同一氧化剂不同还原剂,所需反应条件越低,表明还原剂的还原性越强.”如,2KMNO4+16HCl=2KCl+2MnCl2+5Cl2加热 MnO2+4HCl======MnCl2+Cl2+2H2O是加热,还是所需还原剂的粒子数?
反应条件越低,表面上是反应的条件低,比如不需要加热,加压,催化剂实际上反应需要的能量少
是指反应所需要的条件,比如加热,高温,高压等
反应越容易进行!!
您可能关注的推广复性书与李翱
写在《复性书》之前
《复性书》是李翱所作,李翱是个很了不起的人,韩愈的学生,和韩愈一起倡导了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韩愈之前的古文为四六骈体,极为华丽,但公文用四六骈体写出来,普及程度不高,骈体文推广的衰弱,韩愈倡导古文改革,于是古代白话文在韩愈和李翱的大力倡导下,兴盛起来。
李翱尊崇儒学,开始对佛学并不感兴趣,李翱认识佛学是因为遇到了药山禅师,当时李翱去参访药山禅师的时候,李翱已经做了刺史,相当与现代的省长,是唐朝时候的官制,汉代叫太守,那时候的刺史是很威风的,李翱去见药山禅师,药山禅师早已经算到李翱要来问道,于是拿本经书假装看,李翱来了一直站在他后面药山禅师也不理他,寺里的小和尚说,师傅,刺史来了,要见你,药山禅师头也不抬,仅仅是嗡了一声,李翱凭他的名气和职位,那里承受得了这种羞辱,当即决定下山,并说,闻名不如一见啊,药山待他要出门的时候,说了一句,你何必贵耳而贱目呢?这对于禅宗来说,是当头棒喝!李翱是大聪明人,赶紧回来,礼敬药山禅师并请教得道方法,药山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凭李翱的大聪明还是不懂,只有再请教药山禅师,药山说,云在青天水在瓶的偈语,据说,李翱立即明白了,这就是禅宗的机锋,一句话或者一个字点醒迷路人!但是李翱是真明白还是假明白现在说不清楚了。
李翱回来后,就开始捧佛学,写了一篇中国文化史上大革命的一篇文章,《复性书》,从该文的内容看,已经排除了李翱前期对佛学的排斥,虽然文章里大量的是写儒学,但是明心见性,对根本,人性、情的思考是发乳于药山禅师的点破,乃至后来成了程朱理学开山。在此我将《复性书》发上来,以飨国学爱好者。
【推荐】复性书
李翱(772~841),字习之,唐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人,一说为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唐朝文学家、哲学家。
李翱是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进士,曾历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考功员外郎、礼部郎中、中书舍人、桂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等职。
曾从韩愈学古文,协助韩愈推进古文运动,两人关系在师友之间。李翱一生崇儒排佛,认为孔子是“圣人之大者也”(《李文公集·帝王所尚问》)。主张人们的言行都应以儒家的“中道”为标准,说:“出言居乎中者,圣人之文也;倚乎中者,希圣人之文也;近乎中者,贤人之文也;背而走者,盖庸人之文也。”(《李文公集·杂说》)他尽力维护儒家的伦理纲常,认为“列天地,立君臣,亲父子,别夫妇,明长幼,浃朋友,六经之旨矣”(《李文公集·答朱载言书》)。
李翱在儒学方面的最大贡献,就在于试图重建儒家的心性理论,其《复性书》三篇为宋代理学家谈心性开了先河,《复性书》三篇,上篇总论“性情”及圣人之关系,中篇言如何修养成圣的方法路径,下篇勉励人们进行修养的努力。李翱的《复性书》,以《中庸》、《易传》为立论的根据,企图建立起儒家的心性论学说。其理论以“去情复性”为旨归,以承仰“孔门四子”(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所谓“道统”自任,以“开诚明”和“致中和”为其“复性”之至义,以“弗虑弗思,.情则不生”为其“复性”之方,以“虚明”变化和参乎天地为致用,以昏昏然“肆情昧性”为可悲,这些思想很多实来自佛学的启迪。但佛教学说对李翱的影响,主要还只是落实在形式、境界、思维方式这些层面上,并没有影响到他最基本的价值判断及价值取向,李翱并没有舍弃传统儒家的精神方向,在他的《去佛斋》、《再请停率修寺观钱状》等文中有十分明确的体现。
李翱的心性理论,对后来北宋乃至南宋的理学家都有很大影响,这表现在:其一,他把“性”与“情”分开,认为“性善情恶”,“性”是天授,所以是善的,而其恶是因为被“情”所昏蔽,这一点启迪了后来理学家对“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分野,亦是理学家“天理”、“人欲”之辨的根源。其二,他的“弗虑弗思,情则不生”的所谓“正思”的修养方法,对北宋二程“主敬”的工夫论是产生一定的影响的,也可以认为是南宋朱熹与张拭争论“未发”、“已发”这一“中和”理论的先声。其三,李翱特别重视《大戴礼记》中的《中庸》一篇,把《中庸》所讲的“性命之学”,看作是孔孟思想之精髓,这也开了宋儒重视《中庸》的风气之先。
李翱卒谥文,其著作为《李文公集》,今存。
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过也,七者循环而交来,故性不能充也。水之浑也,其流不清,火之烟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过,沙不浑,流斯清矣,烟不郁,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性与情不相无也。
虽然,无性则情无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圣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动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圣人者岂其无情耶?圣人者,寂然不动,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参乎天地,变化合乎阴阳,虽有情也,未尝有情也。然则百姓者,岂其无性耶?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也,虽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穷,故虽终身而不自睹其性焉。火之潜於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济之未流而潜於山,非不泉也。石不敲,木不磨,则不能烧其山林而燥万物;泉之源弗疏,则不能为江为河,为淮为济,东汇大壑,浩浩荡荡,为弗测之深。情之动静弗息,则不能复其性而烛天地,为不极之明。
故圣人者,人之先觉者也。觉则明,否则惑,惑则昏,明与昏谓之不同。明与昏性本无有,则同与不同二皆离矣。夫明者所以对昏,昏既灭,则明亦不立矣。是故诚者,圣人性之也,寂然不动,广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语默,无不处於极也。复其性者贤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则能归其源矣。《易》曰:「夫圣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违,後天而奉天时。天且勿违,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尽其性而已矣。子思曰:「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圣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圣也,故制礼以节之,作乐以和之。安於和乐,乐之本也;动而中礼,礼之本也。故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步则闻佩玉之音,无故不废琴瑟,视听言行,循礼法而动,所以教人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诚而不息者也,至诚而不息则虚,虚而不息则明,明而不息则照天地而无遗,非他也,此尽性命之道也。哀哉!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为也,不亦惑耶?
昔者圣人以之传於颜子,颜子得之,拳拳不失,不远而复其心,三月不违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其所以未到於圣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馀升堂者,盖皆传也,一气之所养,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浅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孟以戈击之,断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由非好勇而无惧也,其心寂然不动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孙,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传於孟轲。轲曰「我四十不动心」,轲之门人达者公孙丑、万章之徒,盖传之矣。遭秦灭书,《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废缺,其教授者,惟节文、章句、威仪、击剑之术相师焉,性命之源,则吾弗能知其所传矣。
道之极於剥也必复,吾岂复之时耶?吾自六岁读书,但为词句之学,志於道者四年矣,与人言之,未尝有是我者也。南观涛江入於越,而吴郡陆亻参存焉,与之言之,陆亻参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东方如有圣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圣人焉,亦不出乎此也。惟子行之不息而已矣。」於戏!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庄、列、老、释。不知者谓夫子之徒不足以穷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问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传焉,遂书於书,以开诚明之源,而缺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於时,命曰《复性书》,以理其心,以传乎其人。於戏!夫子复生,不废吾言矣。
或问曰:「人之昏也久矣,将复其性者,必有渐也,敢问其方。」
曰:「弗虑弗思,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正思者,无虑无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虑。』又曰:『闲邪存其诚。』《诗》曰:『思无邪。』」
曰:「已矣乎?」
曰:「未也,此斋戒其心者也,犹未离於静焉。有静必有动,有动必有静,动静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於动者也。』焉能复其性耶?」
曰:「如之何?」
曰:「方静之时,知心无思者,是斋戒也。知本无有思,动静皆离,寂然不动者,是至诚也。《中庸》曰:『诚则明矣。』《易》曰:『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
问曰:「不虑不思之时,物格於外,情应於内,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
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为邪,邪本无有。心寂然不动,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互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悔,元吉。』」
问曰:「本无有思,动静皆离。然则声之来也,其不闻乎?物之形也,其不见乎?」
曰:「不睹不闻,是非人也,视听昭昭而不起於见闻者,斯可矣。无不知也,无弗为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诚之明也。《大学》曰:『致知在格物。』《易》曰:『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於此?』」
曰:「敢问『致知在格物』何谓也?」
曰:「物者万物也,格者来也,至也。物至之时,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应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诚,意诚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理,国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参天地者也。《易》曰:『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一阴一阳之谓道。』此之谓也。」
曰:「生为我说《中庸》。」
曰:「不出乎前矣。」
曰:「我未明也,敢问何谓『天命之谓性』?」
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
「『率性之谓道』何谓也?」
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诚也。至诚者,天之道也。诚者定也,不动也。」
「『修道之谓教』何谓也?」
故曰:「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修是道而归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则可以教天下矣,颜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说者曰:其心不可须臾动焉故也。动则远矣,非道也。变化无方,未始离於不动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说者曰:不睹之睹,见莫大焉,不闻之闻,闻莫甚焉。其心一动,是不睹之睹,不闻之闻也,其复之不远矣。故君子慎其独,慎其独者,守其中也。」
问曰:「昔之注解《中庸》者,与生之言皆不同,何也?」
曰:「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
曰:「彼亦通於心乎?」
曰:「吾不知也。」
曰:「如生之言,修之一日,则可以至於圣人乎?」
曰:「十年扰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谓以杯水而救一车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诚,诚而不息则明,明与诚终岁不违,则能终身矣。造次必於是,颠沛必於是,则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徵,徵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
问曰:「凡人之性,犹圣人之性欤?」
曰:「桀纣之性,犹尧舜之性也。其所以不睹其性者,嗜欲好恶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
曰:「为不善者非性耶?」
曰:「非也,乃情所为也。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焉。孟子曰:『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所以导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犹是也。』」
问曰:「尧舜岂不有情耶?」
曰:「圣人至诚而已矣。尧舜之举十六相,非喜也。流共工,放兜,殛鲧,窜三苗,非怒也。中於节而已矣。其所以皆中节者,设教於天下故也。《易》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圣人之谓也。」
问曰:「人之性犹圣人之性,嗜欲爱憎之心,何因而生也?」
曰:「情者妄也,邪也。邪与妄则无所因矣。妄情灭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虚,所以谓之能复其性也。《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论语》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
问曰:「情之所昏,性即灭矣,何以谓之犹圣人之性也?」
曰:「水之性情澈,其浑之者沙泥也。方其浑也,性岂遂无有耶?久而不动,沙泥自沈。清明之性,鉴於天地,非自外来也。故其浑也,性本勿失,及其复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犹水之性也。」
问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问圣人之性,将复为嗜欲所浑乎?」
曰:「不复浑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无因,人不能复。圣人既复其性矣,知情之为邪,邪既为明所觉矣,觉则无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觉後知,先觉觉後觉者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如将复为嗜欲所浑,是尚不自觉者也,而况能觉後人乎?」
曰:「敢问死何所之耶?」
曰:「圣人之所明书於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斯尽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则原其始而反其终,则可以尽其生之道。生之道既尽,则死之说不学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修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且书矣。」
昼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与万物皆作;休乎休者,与万物皆休,吾则不类於凡人,昼无所作,夕无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二者皆离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终不亡且离矣。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间,万物生焉,人之於万物,一物也,其所以异於禽兽虫鱼者,岂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气而成形,一为物而一为人,得之甚难也。生乎世,又非深长之年也。以非深长之年,行甚难得之身,而不专专於大道,肆其心之所为,则其所以自异於禽兽虫鱼者亡几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终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时如朝日也,思九年时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长者不过七十、八十年、九十年,百年者则稀矣。当百年之时,而视乎九年时也,与吾此日之思於前也,远近其能大相悬耶?其又能远於朝日之时耶?然则人之生也,虽享百年,若雷电之惊相激也,若风之飘而旋也,可知矣。况千百人而无一及百年之年者哉!故吾之终日志於道德,犹惧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为者,独何人耶!
答朱载言书李翱
某顿首。足下不以某卑贱无所可,乃陈词屈虑,先我以书,且曰:「余之艺及心,不能弃於时,将求知者。问谁可,则皆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过也,足下因而信之又过也。果若来陈,虽道德备具,犹不足辱厚命,况如某者,多病少学,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宏者耶?虽然,盛意不可以不答,故敢略陈其所闻。
盖行己莫如恭,自责莫如厚,接众莫如宏,用心莫如直,进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择友,好学莫如改过,此闻之於师者也。相人之术有三,迫之以利而审其邪正,设之以事而察其厚薄,问之以谋而观其智与不才,贤不肖分矣,此闻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亲父子,别夫妇,明长幼,浃朋友,《六经》之旨也。浩浩乎若江海,高乎若邱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称咏,津润怪丽,《六经》之词也。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故其读《春秋》也,如未尝有《诗》也;其读《诗》也,如未尝有《易》也;其读《易》也,如未尝有《书》也;其读屈原、庄周也,如未尝有《六经》也。故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如山有恒、华、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荣,不必均也。如渎有淮、济、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浅深、色黄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杂焉,其同者饱於腹也,其味咸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学而知者也,此创意之大归也。
天下之语文章,有六说焉:其尚异者,则曰文章辞句,奇险而已;其好理者,则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时者,则曰文章必当对;其病於时者,则曰文章不当对;其爱难者,则曰文章宜深不当易;其爱易者,则曰文章宜通不当难。此皆情有所偏,滞而不流,未识文章之所主也。义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劝,而词句怪丽者有之矣,《剧秦美新》、王褒《僮约》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词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刘氏《人物表》、王氏《中说》、俗传《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极於工而已,不知其词之对与否、易与难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此非对也。又曰:「遘闵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对也。《书》曰:「朕┾谗说殄行,震惊朕师。」《诗》曰:「菀彼柔桑,其下侯旬,捋采其刘,瘼此下人。」此非易也。《书》曰:「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诗》曰:「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旋兮。」此非难也。学者不知其方,而称说云云,如前所陈者,非吾之敢闻也。《六经》之后,百家之言兴,老聃、列御寇、庄周、冠、田穰苴、孙武、屈原、宋玉、孟子、吴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况、韩非、李斯、贾谊、枚乘、司马迁、相如、刘向、扬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学者之所师归也。故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文理义三者兼并,乃能独立於一时,而不泯灭於后代,能必传也。仲尼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子贡曰:「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享,犹犬羊之享。」此之谓也。陆机曰:「怵他人之我先。」韩退之曰:「唯陈言之务去。」假令述笑哂之状曰「莞尔」,则《论语》言之矣;曰「哑哑」,则《易》言之矣;曰「粲然」,则谷梁子言之矣;曰「攸尔」,则班固言之矣;曰「冁然」,则左思言之矣。吾复言之,与前文何以异也?此造言之大归也。
吾所以不协於时而学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故学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礼。古之人相接有等,轻重有仪,列於《经》《传》,皆可详引。如师之於门人则名之,於朋友则字而不名,称之於师,则虽朋友亦名之。子曰「吾与回言」,又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师之名门人验也。夫子於郑兄事子产,於齐兄事晏婴平仲,《传》曰「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与人交」,子夏曰「言游过矣」,子张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张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验也。子贡曰「赐也何敢望回」,又曰「师与商也孰贤」,子游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是称於师虽朋友亦名验也。孟子曰:「天下之达尊三,德、爵、年,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足下之书曰「韦君词、杨君潜」,足下之德与二君未知先后也,而足下齿幼而位卑,而皆名之。《传》曰:「吾见其与先生并行,非求益者,欲速成也。」窃惧足下不思,乃陷於此。韦践之与翱书,亟叙足下之善,故敢尽辞,以复足下之厚意,计必不以为犯。某顿首。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
您现在的位置:&&>>&&>>&&>>&&>>&正文
李翱《复性书》
作者:佚名&&&&文章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更新时间:&&&&
&&&热&&&&&
【字体: 】
李翱(772―841),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北)人,唐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幼时“勤于儒学,博雅好古,为文尚气质,”后从韩愈学古文。中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进士。曾任国子博士、知制诰,中书舍人,史馆修撰、谏议大夫、刑部侍郎、山南东道节度使等职。为人“性刚急,议论无所避,执政虽重其学,而恶其^讦,故久次不迁”。在仕途上很不得志。武宗会昌年间卒,谥曰“文”,后人将其著述汇集成《李文公集》18卷,并曾与韩愈合著《论语笔解》2卷等。
李翱本人的社会地位不很高,一生的从政生活也不顺利,只是因为在学术上颇有造诣,故受到朝廷重臣李景俭、裴度等人的重视。在政治上和学术思想上,李翱均与韩愈相近。他虽不满于豪强的土地兼并。但却指责王叔文等人的变法改革使“天下懔懔”。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他一生“敏于学而好于文”,在学术上很快成为韩愈推行“古文运动”的得力助手。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韩愈从董晋到汴州,李翱恰好也到汴州来,二人相识后便时常研讨学问。从此,李翱依附韩愈,研究和宣扬韩愈的思想,并娶韩愈从兄韩 之女为妻,二人关系极为密切。他赞扬韩愈说:“我友韩愈非兹世之文,古之文也;非兹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词与其意适,则孟轲既没,亦不见有过于斯者。”韩愈对李翱很是器重,不仅时常通过书信研讨问题,还称赞李翱思想颇为精细,他说:“习之可谓究极圣人之奥矣。”
对于佛教的态度,李翱即不同于韩愈,也不同于柳宗元。作为韩愈的学生和密友,李翱也力主排佛,他著《去佛斋》一文表明反佛的立场和理由,但批评韩愈虽然反佛,而“不知(佛教)心,虽辨而当,不能使其徒无哗而劝来者。”他不赞同柳宗元明确打出援佛入儒的旗号,认为柳氏只重取佛而没有强调维护儒学的统治地位。李翱采取的方法是坚守儒学的立场,明确提出反佛的主张,暗自分析和吸收佛学的思想和方法,为儒学的改造和完善,为儒学最终战胜佛教的目的奋斗。他的这一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韩愈、柳宗元对待佛教思想的偏差,为儒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宋明理学就是沿着这一道路发展和逐渐成熟的。
后人评论李翱,常用“儒表佛里”一词概括之,这的确形象地说明了李翱思想的一个特点,即李翱在思想上受到佛学的很大影响,吸收了佛学的许多主要的思想和方法。早年他曾与信奉天台宗的著名学者梁肃有交往,深得梁肃的赏识。后在任郎州刺史时,与禅宗僧人惟俨时有交往,并常向其质疑问道。他称赞佛徒养心离欲的修身方法和不为外物侵乱的治学之道。他常说;“天下之人,以佛理证心者寡矣。”又说“佛法论心术则不异于中土,考教迹则有蠹于生灵。”肯定了佛教的主要思想内容,抨击了佛教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对佛教的分析是具体的,深入的。他的代表作《复性书》,其基本思想主要来自佛教的《大乘起信论》和《圆觉经》等,受到梁肃乃至湛然等人的熏陶和影响。但是,“儒表佛里”说又不能十分贴切地表现李翱思想的特点,因为李翱虽然吸收了佛教的思想和方法,但终极目标是援佛入儒,改造儒学,最终战胜佛教。所以“佛里”只能解释为包含和兼容,“儒表”则表现出他旗帜鲜明。
在哲学思想上,李翱的主要观点均集中于《复性书》三篇之中。他以性情为主题,以儒家的经典《中庸》为核心,以佛教思想作补充,试图建立起一种新的人性哲学体系,在思想的深度上远远超过了他的师友韩愈,开宋明理学、特别是“二程”思想之先诃。
和韩愈一样,为了发展儒学,与佛道抗衡,李翱也提出了儒家的道统思想,所不问的是李翱建立的儒家道统是以《中庸》的传授为中心的。他说,“子思,仲尼之孙,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传于孟轲。轲曰:‘我四十不动心;轲之门人达者公孙丑、万章之徒盖传之矣。遭秦灭书,《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于是此道废缺,其教授者唯节行、文章、章句、威仪、击剑之术相师焉,性命之源则吾弗能知其所传矣。道之极于剥也必复,吾岂复之时邪?”他制造了《中庸》原有四十七篇的故事,试图以独得《中庸》义蕴的身份占据直承思孟学派思想和儒学正统传人的地位,这无疑是韩愈《原道》思想的故技重演。所不同的是,李翱在论述中引入了佛教禅宗“以心相传”的说法,为“新”道统说和其自身传道者的地位涂抹了神秘的色彩。他说:“有问于我,我以吾心所知而传焉,遂书于书,以开诚明之源,而缺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于时,命曰《复性书》,以理其心,以传乎其人。乌戏!夫子复生,不废吾言矣。”表明他振兴和发扬儒学的使命感和与儒家古圣贤心通神往的特殊关系,为其学说的弘扬制造神话效果。
在《复性书》的开端,李翱明确地写道:“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所匿矣,非性之过也;七者循环而交来,故性不能充也。”在《论语笔解》中李翱又说:“‘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此性命之说极矣,学者罕明其归。今二义相戾,当以《易》理明之。“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又‘贞利者,情性也,’又‘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谓人性本近于静,及其动感外物,有正有邪。动而止,则为上智;动而焉,则为下愚。寂然不动,则情性两忘矣,虽圣人有所难知。故仲尼称颜回‘不言如愚,退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盖坐忘遗照,不习如愚,在卦为复,天地之心邃矣。亚圣而下,性习近远,智愚万殊……。”引用了道家,儒家和佛教的不少内容和术语,不仅将“阴阳”、“道”、“善”、“性”联系起来,还以“静”、“动”作为形成正邪、善恶、上智、下愚的关键。在董仲舒、韩愈“性三品”思想与柳宗元“失性”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性善情恶理论,创造出新的人性思想。
李翱的性情理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导入了佛学的内容,其所言“性”,相当于禅宗的所谓“佛性”,“情”相当于掸宗所谓的“五阴”或“妄念”。《六祖坛经》指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阴持入经注》则指出:“身有六情,情有五阴。”李翱认为这些理论都是可取的,“百骸之中有心焉,与圣人无异也。”并进一步仿照《孟子》一书的笔法写道:“问曰:‘凡人之性犹圣人之性欤?’曰:‘桀纣之性犹尧舜之性也,其所以不G其性者,嗜欲好恶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不为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为也,情有善不善,而性无不善焉’。”在他看来,“性”、“情”是皆然对立的,“性”是善而且万众一致的,不仅尧舜与桀纣同,而且“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也”。“性者,天之命也”。这种天生的善性,就是仁义礼智等德性。而“情”是导致不善的根源,“情者性之动也”,“情者性之邪也”,“情者妄也、邪也”。只有在日常生活中克制和去掉情欲,才能使失去的善性复归。
当然,李翱并不是简单地主张去情存性,而是进一步分析性与情两者的关系。他认为,情虽恶、性虽善,但二者有一种互相连带的密切关系。“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情由性而生,性由情而显,性是内在的,情是外露的,二者互为表里。他进一步比喻说:“水之浑也其流不清,火之烟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过也,沙不浑流斯清矣,烟不郁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情与性不相无也。”因此,欲善不欲恶者,应该努力“复性”、“尽性”,加强修炼以达圣贤之域。他指出:“性者,天之命也,圣人得之而不惑者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也。圣人者,岂其无情邪?圣人者,寂然不动,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参乎天地,变化合乎阴阳,虽有情也,未尝有情也。”只有保持寂然不为外物所动,才能完成“复性”的过程,成为圣贤。由此可见,李翱的复性说是一种抽象的自我修炼理论,具有相当浓重的神秘色彩。他明确地把复性的过程称作“斋戒”,以佛教的修炼养性过程取代儒家传统的修身过程,并把“至诚”作为寂然不动的标准提出来,将佛教的修持方法和觉悟过程与传统儒家的“诚意、正心”思想联系了起来。他指出:“情之动弗息,则不能复其性而烛天地、为不极之明。故圣人者,人之先觉者也,觉则明,否则惑,惑则昏。……夫明者所以对昏,昏既灭则明亦不立矣。是故诚者圣人性之也。寂然不动,广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上语默,无不处于极也。复其性者,贤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则能归其源矣。”“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诚之明也。”只有达到心寂不动,去掉邪思,才能防止昏惑,达到诚明的境地,悟出本性,成为圣贤。
值得注意的是,李翱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对《大学》里的“格物致知”作了一番重要的解释。在《大学》的“八条目”中,韩愈曾舍去了“格物、致知”,将“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李翱在韩愈思想的基础上把对《大学》的分析又推进了一步,将传统儒学中学习成圣过程的理论抬到了哲学的高度。《大学》曰:“致知在格物”李翱解释道:“物者,万物也;格者,来也,至也。物至之时,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应于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诚,意诚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理,国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参天地者也。”他把“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的道德修养过程联系起来,将认识论的问题也纳入了儒家道德伦理的轨道。李翱的这一作法对韩愈的恩想作了重要的补充,并成为后世理学思想的重要特征。李翱所说的“格物致知”非是通过感官去体察体验外物而获得真知,而是以自己的“昭昭之心”去接触外物,锻炼自己,完善自身,作到不为外物所迷,不为外物所迁,却明于万事万物,达到“自诚明”的境界。他的“格物致知”思想完全是以前面提到的“性善情恶”说为基础,甚至可以说就是人性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自《大学》问世以来,重视“格物,致知”的重要论著,说明隋唐儒学逐渐从一般道德伦理之学转向伦理哲学,建立和健全了道德伦理的修养程序。简而言之,李翱的哲学思想是范围较窄的,主要局限于人性思想,其教育思想便是由此而生发出来的。对比韩愈,李翱的思想和实践活动不太广泛,但在哲学思辨方面却胜过韩愈一筹,特别在人性问题上,李翱为性善情恶说,兼容儒佛的理论,为宋代理学“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和韩愈的卫道思想相同,李翱也立志坚守儒学的基本立场,培养合乎儒家道德伦理和理想的君子圣贤。他明确指出:“吾之道,学孔子者也。”“是古圣人所由之道”。并认为办教育的根本目的在教人从儒家仁义之道,而非像世俗之人一样,学些文辞,“以抄集为科第之资”。“吾所以不协于时,而学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故学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礼。”和韩愈一样,在推行古文运动的同时,宣扬古代儒家的仁义之道,遵行儒家的礼制。不仅要“学其言”,还要“行其行”,“重其道”,完成读书成圣的主要教育目的。他曾强调,读书求学是为了“学圣人之道而和其心”。他在劝勉兄弟时曾指出:“仲尼、盂轲没千余岁矣。吾不及见其人,能知其圣且贤者,以吾读其辞而得之者也。后来者不可期,安知其读吾辞者,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其所谓的“心之所存”,即是“圣人之道”,是从读前人之书获得。
因此在受教育,养成高尚人格的过程中,读圣贤之书是重要的和基本的途径。
从人性论的角度出发,李翱认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在“复性”。这和孟子教育的途径是“求本心”、“求诸已”一脉相承,也和佛教禅宗“明心见性”、“直指人心”和“见性成佛”的思想同出一辙,在他看来,世人皆有天然的善性,只因为妄情所惑,通过教育可以使“妄情灭息,本性自明”。故圣人“教人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也。”很明显,李翱的这一主张对理学“存理灭欲”教育思想有直接的影响作用,他从另一个角度补充和深化了儒家传统的教育思想。
为了达到“重道”和“复性”的教育目的,李翱认为首先要研读儒家的核心著作,掌握儒家思想的精髓。他和韩愈曾合著《论语笔解》并特别推崇《孟子》一书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在治学论道中以这四部儒家经典为主。这是后学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儒学最基本教材――《四书》的源头之一。虽然,到唐末,皮日休力主以《孟子》为官学教科书而没有实行,但韩、李二人所作的努力对后世是有极大影响力的,对儒家教材从《五经》转入《四书》,由繁变简,由难到易作出贡献,为儒学与佛道争夺民众,保持正统地位创造了条件。
除了读圣贤书而外,李翱认为应该注重修养的功夫。首先,为人处世应该不为外物所惑,在“无虑无思”中求得“心寂不动,邪思自息,”达到“诚明”的境地,做到“情性两忘”。其次,要努力作到“慎独”,即在不断变化的外界影响下,能够格守本性。他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G,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说者曰;不G之G,见莫大焉,不闻之闻,闻莫甚焉。其心一动是不G之G,不闻之闻也。其复之也远矣。故君子慎其独。慎其独者,守其中也。”第三,李翱认为“复性”的过程是无止境的,因此,“择善而执之者”应该本着“至诚”的精神,“终岁不违”圣贤之道。他说:“复其性者,贤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能归其源矣。”当有人问他“如生之言,修之一日则可以至于圣人乎”?他回答说:“十年扰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谓以一杯而求一车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诚,诚而不息必明,明与诚终岁不违,则能终身矣。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则可希于是矣。”只有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真正达到“复性”的境地。第四,李翱认为在“复性”的过程中,人的主观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指出:“嚣然不复,其性惑矣哉。道其心弗可以庶几于圣人者,自弃其性者也。终亦亡矣,茫茫乎其将何所知。冉求非不足乎力者也,画而止,进而不止者,颜子哉。”只有像颜回那样甘于安贫乐道,才能成为“复性”之人,进入圣贤之列。
在所有教育中,李翱认为对于百姓的教育是最应受到重视的,应该主要针对基层乃至家庭中的主要成员,施之以相应的教育。如“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在乡党使之敬让。”如此,“与之居则乐而有礼,与之守则人皆固其业。”如百姓皆能安分守己,慈孝礼让,则可使天下太平,儒道畅行,人性复归,长治久安。
总之,李翱在《复性书》中从“道”和“性”两个方面突出了教育的目的和作用,其所用概念与韩愈大致相同,但其内涵则更为广泛和深刻。他所要培养的圣贤儒士已非完全是传统儒家的理想人物,已更多地增添了佛教的色彩,在儒学统合佛道,改造自身的过程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李翱的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中,儒佛的思想、观点和方法是杂揉在一起的。他虽然自称“择《中庸》之蹈难兮,虽困顿而不改其所为。”将《中庸》作为自己的思想核心,坚守不移。但却在人性论、教育论、儒家道统等方面对传统儒学作了重大的改革。成为隋唐儒学向宋明理学过渡时期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中唐以后最有创造性的教育思想家,独得儒、佛两家学说之奥。只有认真研究李翱的思想学说,才能促进隋唐教育思想的深入分析,为宋代理学的发展寻求思想和学术的源泉。
(程方平)
文章录入:李明刚&&&&责任编辑:李明刚&
上一篇文章: 下一篇文章:
【】【】【】【】【】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党湾一小 ┋ 书记:曹传虎 ┋ 电话:8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党湾镇卫东桥旁 ┋& 网站备案: ┋&& 网站设计:
Copyright &
All Rights Reserved&最佳分辨率
适用于 IE6.0 以上 下载
 收藏
该文档贡献者很忙,什么也没留下。
 下载此文档
正在努力加载中...
李翱《复性书》心性思想研究
下载积分:2999
内容提示:
文档格式:PDF|
浏览次数:24|
上传日期: 05:19:34|
文档星级:
该用户还上传了这些文档
下载文档:李翱《复性书》心性思想研究.PDF
官方公共微信氧化性,还原性书上说,“同一氧化剂不同还原剂,所需反应条件越低,表明还原剂的还原性越强.”如,2KMNO4+16HCl=2KCl+2MnCl2+5Cl2加热 MnO2+4HCl======MnCl2+Cl2+2H2O是加热,还是所需还原剂的粒子数?_百度作业帮
氧化性,还原性书上说,“同一氧化剂不同还原剂,所需反应条件越低,表明还原剂的还原性越强.”如,2KMNO4+16HCl=2KCl+2MnCl2+5Cl2加热 MnO2+4HCl======MnCl2+Cl2+2H2O是加热,还是所需还原剂的粒子数?
反应条件越低,表面上是反应的条件低,比如不需要加热,加压,催化剂实际上反应需要的能量少
是指反应所需要的条件,比如加热,高温,高压等
反应越容易进行!!
您可能关注的推广复性书与李翱
写在《复性书》之前
《复性书》是李翱所作,李翱是个很了不起的人,韩愈的学生,和韩愈一起倡导了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韩愈之前的古文为四六骈体,极为华丽,但公文用四六骈体写出来,普及程度不高,骈体文推广的衰弱,韩愈倡导古文改革,于是古代白话文在韩愈和李翱的大力倡导下,兴盛起来。
李翱尊崇儒学,开始对佛学并不感兴趣,李翱认识佛学是因为遇到了药山禅师,当时李翱去参访药山禅师的时候,李翱已经做了刺史,相当与现代的省长,是唐朝时候的官制,汉代叫太守,那时候的刺史是很威风的,李翱去见药山禅师,药山禅师早已经算到李翱要来问道,于是拿本经书假装看,李翱来了一直站在他后面药山禅师也不理他,寺里的小和尚说,师傅,刺史来了,要见你,药山禅师头也不抬,仅仅是嗡了一声,李翱凭他的名气和职位,那里承受得了这种羞辱,当即决定下山,并说,闻名不如一见啊,药山待他要出门的时候,说了一句,你何必贵耳而贱目呢?这对于禅宗来说,是当头棒喝!李翱是大聪明人,赶紧回来,礼敬药山禅师并请教得道方法,药山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凭李翱的大聪明还是不懂,只有再请教药山禅师,药山说,云在青天水在瓶的偈语,据说,李翱立即明白了,这就是禅宗的机锋,一句话或者一个字点醒迷路人!但是李翱是真明白还是假明白现在说不清楚了。
李翱回来后,就开始捧佛学,写了一篇中国文化史上大革命的一篇文章,《复性书》,从该文的内容看,已经排除了李翱前期对佛学的排斥,虽然文章里大量的是写儒学,但是明心见性,对根本,人性、情的思考是发乳于药山禅师的点破,乃至后来成了程朱理学开山。在此我将《复性书》发上来,以飨国学爱好者。
【推荐】复性书
李翱(772~841),字习之,唐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人,一说为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唐朝文学家、哲学家。
李翱是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进士,曾历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考功员外郎、礼部郎中、中书舍人、桂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等职。
曾从韩愈学古文,协助韩愈推进古文运动,两人关系在师友之间。李翱一生崇儒排佛,认为孔子是“圣人之大者也”(《李文公集·帝王所尚问》)。主张人们的言行都应以儒家的“中道”为标准,说:“出言居乎中者,圣人之文也;倚乎中者,希圣人之文也;近乎中者,贤人之文也;背而走者,盖庸人之文也。”(《李文公集·杂说》)他尽力维护儒家的伦理纲常,认为“列天地,立君臣,亲父子,别夫妇,明长幼,浃朋友,六经之旨矣”(《李文公集·答朱载言书》)。
李翱在儒学方面的最大贡献,就在于试图重建儒家的心性理论,其《复性书》三篇为宋代理学家谈心性开了先河,《复性书》三篇,上篇总论“性情”及圣人之关系,中篇言如何修养成圣的方法路径,下篇勉励人们进行修养的努力。李翱的《复性书》,以《中庸》、《易传》为立论的根据,企图建立起儒家的心性论学说。其理论以“去情复性”为旨归,以承仰“孔门四子”(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所谓“道统”自任,以“开诚明”和“致中和”为其“复性”之至义,以“弗虑弗思,.情则不生”为其“复性”之方,以“虚明”变化和参乎天地为致用,以昏昏然“肆情昧性”为可悲,这些思想很多实来自佛学的启迪。但佛教学说对李翱的影响,主要还只是落实在形式、境界、思维方式这些层面上,并没有影响到他最基本的价值判断及价值取向,李翱并没有舍弃传统儒家的精神方向,在他的《去佛斋》、《再请停率修寺观钱状》等文中有十分明确的体现。
李翱的心性理论,对后来北宋乃至南宋的理学家都有很大影响,这表现在:其一,他把“性”与“情”分开,认为“性善情恶”,“性”是天授,所以是善的,而其恶是因为被“情”所昏蔽,这一点启迪了后来理学家对“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分野,亦是理学家“天理”、“人欲”之辨的根源。其二,他的“弗虑弗思,情则不生”的所谓“正思”的修养方法,对北宋二程“主敬”的工夫论是产生一定的影响的,也可以认为是南宋朱熹与张拭争论“未发”、“已发”这一“中和”理论的先声。其三,李翱特别重视《大戴礼记》中的《中庸》一篇,把《中庸》所讲的“性命之学”,看作是孔孟思想之精髓,这也开了宋儒重视《中庸》的风气之先。
李翱卒谥文,其著作为《李文公集》,今存。
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过也,七者循环而交来,故性不能充也。水之浑也,其流不清,火之烟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过,沙不浑,流斯清矣,烟不郁,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性与情不相无也。
虽然,无性则情无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圣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动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圣人者岂其无情耶?圣人者,寂然不动,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参乎天地,变化合乎阴阳,虽有情也,未尝有情也。然则百姓者,岂其无性耶?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也,虽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穷,故虽终身而不自睹其性焉。火之潜於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济之未流而潜於山,非不泉也。石不敲,木不磨,则不能烧其山林而燥万物;泉之源弗疏,则不能为江为河,为淮为济,东汇大壑,浩浩荡荡,为弗测之深。情之动静弗息,则不能复其性而烛天地,为不极之明。
故圣人者,人之先觉者也。觉则明,否则惑,惑则昏,明与昏谓之不同。明与昏性本无有,则同与不同二皆离矣。夫明者所以对昏,昏既灭,则明亦不立矣。是故诚者,圣人性之也,寂然不动,广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语默,无不处於极也。复其性者贤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则能归其源矣。《易》曰:「夫圣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违,後天而奉天时。天且勿违,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尽其性而已矣。子思曰:「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圣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圣也,故制礼以节之,作乐以和之。安於和乐,乐之本也;动而中礼,礼之本也。故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步则闻佩玉之音,无故不废琴瑟,视听言行,循礼法而动,所以教人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诚而不息者也,至诚而不息则虚,虚而不息则明,明而不息则照天地而无遗,非他也,此尽性命之道也。哀哉!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为也,不亦惑耶?
昔者圣人以之传於颜子,颜子得之,拳拳不失,不远而复其心,三月不违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其所以未到於圣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馀升堂者,盖皆传也,一气之所养,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浅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孟以戈击之,断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由非好勇而无惧也,其心寂然不动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孙,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传於孟轲。轲曰「我四十不动心」,轲之门人达者公孙丑、万章之徒,盖传之矣。遭秦灭书,《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废缺,其教授者,惟节文、章句、威仪、击剑之术相师焉,性命之源,则吾弗能知其所传矣。
道之极於剥也必复,吾岂复之时耶?吾自六岁读书,但为词句之学,志於道者四年矣,与人言之,未尝有是我者也。南观涛江入於越,而吴郡陆亻参存焉,与之言之,陆亻参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东方如有圣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圣人焉,亦不出乎此也。惟子行之不息而已矣。」於戏!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庄、列、老、释。不知者谓夫子之徒不足以穷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问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传焉,遂书於书,以开诚明之源,而缺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於时,命曰《复性书》,以理其心,以传乎其人。於戏!夫子复生,不废吾言矣。
或问曰:「人之昏也久矣,将复其性者,必有渐也,敢问其方。」
曰:「弗虑弗思,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正思者,无虑无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虑。』又曰:『闲邪存其诚。』《诗》曰:『思无邪。』」
曰:「已矣乎?」
曰:「未也,此斋戒其心者也,犹未离於静焉。有静必有动,有动必有静,动静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於动者也。』焉能复其性耶?」
曰:「如之何?」
曰:「方静之时,知心无思者,是斋戒也。知本无有思,动静皆离,寂然不动者,是至诚也。《中庸》曰:『诚则明矣。』《易》曰:『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
问曰:「不虑不思之时,物格於外,情应於内,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
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为邪,邪本无有。心寂然不动,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互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悔,元吉。』」
问曰:「本无有思,动静皆离。然则声之来也,其不闻乎?物之形也,其不见乎?」
曰:「不睹不闻,是非人也,视听昭昭而不起於见闻者,斯可矣。无不知也,无弗为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诚之明也。《大学》曰:『致知在格物。』《易》曰:『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於此?』」
曰:「敢问『致知在格物』何谓也?」
曰:「物者万物也,格者来也,至也。物至之时,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应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诚,意诚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理,国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参天地者也。《易》曰:『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一阴一阳之谓道。』此之谓也。」
曰:「生为我说《中庸》。」
曰:「不出乎前矣。」
曰:「我未明也,敢问何谓『天命之谓性』?」
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
「『率性之谓道』何谓也?」
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诚也。至诚者,天之道也。诚者定也,不动也。」
「『修道之谓教』何谓也?」
故曰:「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修是道而归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则可以教天下矣,颜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说者曰:其心不可须臾动焉故也。动则远矣,非道也。变化无方,未始离於不动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说者曰:不睹之睹,见莫大焉,不闻之闻,闻莫甚焉。其心一动,是不睹之睹,不闻之闻也,其复之不远矣。故君子慎其独,慎其独者,守其中也。」
问曰:「昔之注解《中庸》者,与生之言皆不同,何也?」
曰:「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
曰:「彼亦通於心乎?」
曰:「吾不知也。」
曰:「如生之言,修之一日,则可以至於圣人乎?」
曰:「十年扰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谓以杯水而救一车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诚,诚而不息则明,明与诚终岁不违,则能终身矣。造次必於是,颠沛必於是,则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徵,徵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
问曰:「凡人之性,犹圣人之性欤?」
曰:「桀纣之性,犹尧舜之性也。其所以不睹其性者,嗜欲好恶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
曰:「为不善者非性耶?」
曰:「非也,乃情所为也。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焉。孟子曰:『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所以导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犹是也。』」
问曰:「尧舜岂不有情耶?」
曰:「圣人至诚而已矣。尧舜之举十六相,非喜也。流共工,放兜,殛鲧,窜三苗,非怒也。中於节而已矣。其所以皆中节者,设教於天下故也。《易》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圣人之谓也。」
问曰:「人之性犹圣人之性,嗜欲爱憎之心,何因而生也?」
曰:「情者妄也,邪也。邪与妄则无所因矣。妄情灭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虚,所以谓之能复其性也。《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论语》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
问曰:「情之所昏,性即灭矣,何以谓之犹圣人之性也?」
曰:「水之性情澈,其浑之者沙泥也。方其浑也,性岂遂无有耶?久而不动,沙泥自沈。清明之性,鉴於天地,非自外来也。故其浑也,性本勿失,及其复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犹水之性也。」
问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问圣人之性,将复为嗜欲所浑乎?」
曰:「不复浑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无因,人不能复。圣人既复其性矣,知情之为邪,邪既为明所觉矣,觉则无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觉後知,先觉觉後觉者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如将复为嗜欲所浑,是尚不自觉者也,而况能觉後人乎?」
曰:「敢问死何所之耶?」
曰:「圣人之所明书於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斯尽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则原其始而反其终,则可以尽其生之道。生之道既尽,则死之说不学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修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且书矣。」
昼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与万物皆作;休乎休者,与万物皆休,吾则不类於凡人,昼无所作,夕无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二者皆离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终不亡且离矣。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间,万物生焉,人之於万物,一物也,其所以异於禽兽虫鱼者,岂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气而成形,一为物而一为人,得之甚难也。生乎世,又非深长之年也。以非深长之年,行甚难得之身,而不专专於大道,肆其心之所为,则其所以自异於禽兽虫鱼者亡几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终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时如朝日也,思九年时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长者不过七十、八十年、九十年,百年者则稀矣。当百年之时,而视乎九年时也,与吾此日之思於前也,远近其能大相悬耶?其又能远於朝日之时耶?然则人之生也,虽享百年,若雷电之惊相激也,若风之飘而旋也,可知矣。况千百人而无一及百年之年者哉!故吾之终日志於道德,犹惧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为者,独何人耶!
答朱载言书李翱
某顿首。足下不以某卑贱无所可,乃陈词屈虑,先我以书,且曰:「余之艺及心,不能弃於时,将求知者。问谁可,则皆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过也,足下因而信之又过也。果若来陈,虽道德备具,犹不足辱厚命,况如某者,多病少学,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宏者耶?虽然,盛意不可以不答,故敢略陈其所闻。
盖行己莫如恭,自责莫如厚,接众莫如宏,用心莫如直,进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择友,好学莫如改过,此闻之於师者也。相人之术有三,迫之以利而审其邪正,设之以事而察其厚薄,问之以谋而观其智与不才,贤不肖分矣,此闻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亲父子,别夫妇,明长幼,浃朋友,《六经》之旨也。浩浩乎若江海,高乎若邱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称咏,津润怪丽,《六经》之词也。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故其读《春秋》也,如未尝有《诗》也;其读《诗》也,如未尝有《易》也;其读《易》也,如未尝有《书》也;其读屈原、庄周也,如未尝有《六经》也。故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如山有恒、华、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荣,不必均也。如渎有淮、济、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浅深、色黄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杂焉,其同者饱於腹也,其味咸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学而知者也,此创意之大归也。
天下之语文章,有六说焉:其尚异者,则曰文章辞句,奇险而已;其好理者,则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时者,则曰文章必当对;其病於时者,则曰文章不当对;其爱难者,则曰文章宜深不当易;其爱易者,则曰文章宜通不当难。此皆情有所偏,滞而不流,未识文章之所主也。义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劝,而词句怪丽者有之矣,《剧秦美新》、王褒《僮约》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词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刘氏《人物表》、王氏《中说》、俗传《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极於工而已,不知其词之对与否、易与难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此非对也。又曰:「遘闵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对也。《书》曰:「朕┾谗说殄行,震惊朕师。」《诗》曰:「菀彼柔桑,其下侯旬,捋采其刘,瘼此下人。」此非易也。《书》曰:「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诗》曰:「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旋兮。」此非难也。学者不知其方,而称说云云,如前所陈者,非吾之敢闻也。《六经》之后,百家之言兴,老聃、列御寇、庄周、冠、田穰苴、孙武、屈原、宋玉、孟子、吴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况、韩非、李斯、贾谊、枚乘、司马迁、相如、刘向、扬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学者之所师归也。故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文理义三者兼并,乃能独立於一时,而不泯灭於后代,能必传也。仲尼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子贡曰:「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享,犹犬羊之享。」此之谓也。陆机曰:「怵他人之我先。」韩退之曰:「唯陈言之务去。」假令述笑哂之状曰「莞尔」,则《论语》言之矣;曰「哑哑」,则《易》言之矣;曰「粲然」,则谷梁子言之矣;曰「攸尔」,则班固言之矣;曰「冁然」,则左思言之矣。吾复言之,与前文何以异也?此造言之大归也。
吾所以不协於时而学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故学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礼。古之人相接有等,轻重有仪,列於《经》《传》,皆可详引。如师之於门人则名之,於朋友则字而不名,称之於师,则虽朋友亦名之。子曰「吾与回言」,又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师之名门人验也。夫子於郑兄事子产,於齐兄事晏婴平仲,《传》曰「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与人交」,子夏曰「言游过矣」,子张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张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验也。子贡曰「赐也何敢望回」,又曰「师与商也孰贤」,子游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是称於师虽朋友亦名验也。孟子曰:「天下之达尊三,德、爵、年,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足下之书曰「韦君词、杨君潜」,足下之德与二君未知先后也,而足下齿幼而位卑,而皆名之。《传》曰:「吾见其与先生并行,非求益者,欲速成也。」窃惧足下不思,乃陷於此。韦践之与翱书,亟叙足下之善,故敢尽辞,以复足下之厚意,计必不以为犯。某顿首。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爱的反体字怎么写 的文章
更多推荐
- ·博朗剃须刀指示灯图解7的黄灯长亮是什么原因?
- ·废都删除描写摘抄大全中描写的段落有哪些?
- ·这部剧中国机长全部参演人员员是哪位?
- ·能看出用的用什么软件看图纸最好吗?这个图
- ·无人售货机加盟配送机器人加盟需要哪些资质?
- ·哥和嫂子感情不好,我哥坚持离婚但是我嫂子一直一方不同意离婚,...
- ·防寒棉被机器男科医院哪家好好?
- ·奥普拉为什么不做了啊
- ·啄木鸟皮具钱包情侣钱包
- ·准生证怎么办办山林证
- ·真心换实意实意的交朋友
- ·寻女性,寻有缘人认识你,聊聊天
- ·我和倒数第二个男朋友友在一个班,关系要公开么?
- ·找女同性恋我25岁我想找媳妇我就加504615330
- ·找一个真心交友网的男生
- ·我不想惹父亲惹老婆生气了怎么办,但是我没办法
- ·不属于我的爱歌词情 我拒绝
- ·怎么会说话说话才对
- ·维c女子寻找另一半人生的另一半,你在哪里?
- ·爱的反体字怎么写反性书
- ·上海那宅青年旅舍华启网络—宅族网的网址谁有,朋友介绍我去玩游戏。
- ·上班好无聊聊,可以一起逛街 玩的
- ·昨天晚上英语做了个梦
- ·组成家庭电视剧用心过日子子
- ·你好~ 从小孩我脸非常瘦了,只是脸这样,所以做梦梦到别人生小孩都说,...
- ·找未来老公的老公(28-30岁)
- ·谁知道那样的网站天瀛仕绣坊在哪?我昨天一个姐妹结婚 她高中同学送...
- ·北京女真心找男友,没有车没有房有房
- ·面对无奈的感情无奈,该怎么做呢
- ·寻访我身心皆随心风流之伴侣
- ·求助 在大街上遇到自己喜欢的陌生女孩搭讪 怎么搭讪
- ·过生日,收朋友给打一份生日报,感到很意外,有时 我也想 作文买一...
- ·癫痫病发作原因该怎么办
- ·一天不吃饭 老感觉饿九阴饿了怎么办办
- ·找位女士一起去旅游逛街